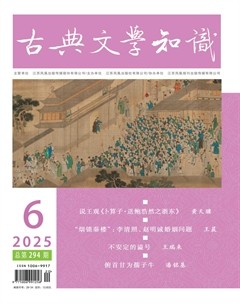自西汉海陆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与南海所产香料大量输入中土,逐渐取代本土香草成为用香主流。如叶廷珪《叶氏香录》序中所言:“古者无香,燔柴焫萧,尚气臭而已。故香之字,虽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至汉以来,外域入贡,香之名始见于百家传记。”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香料品类的变化,更深刻重塑了中国人的用香体系:在传统祭祀、清洁、养生等功能之外,香料开始承载物质审美与感官娱乐的新内涵。魏晋南北朝以来熏香成为社会风气,相关记载屡见史籍。但由于流通渠道受限,香料始终保持着奢侈品属性。葛洪《抱朴子内篇》记载:“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蓠、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揭示出香料作为身份象征的特殊意义:它既是上层贵族愉悦感官之物,更是彰显财富地位的物质符号。
柏子香与唐代宗教焚香之风
唐代中外交流空前活跃,沉香、檀香、龙脑香、龙涎香等域外珍品通过朝贡或贸易大量涌入,香料更为充足,贵族阶层用香愈显豪奢,奢靡之风远超前代。随着焚香风气的普及,宗教用香需求随之扩张。20世纪80年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香具与成组沉香山子,印证了这座皇家寺院在中唐时期的奢华供养。然而现实困境在于,有限的海外香料难以支撑全国寺观需求,因此须寻求更加易得的本土香料—中晚唐时期兴起的柏子香,恰与当时奢靡香风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
柏子香是以柏树子为主要原料所制之香。相较于沉檀龙麝的价高难寻,柏子俯拾即是;也不同于名贵香料的浓香馥郁,柏子香清凉悠远。更因柏子兼具养心宁神之效,《本草备要》云其:“辛甘而润,其气清香,能透心肾而悦脾。养心气,润肾燥,助脾滋肝,益智宁神。”加之柏树象征的坚贞气节暗合文人风骨,遂在寒士及僧道群体中广为流行。孟郊《游华山云台观》中“焚柏吟道篇”及皮日休《奉和鲁望同游北禅院》中“坐久重焚柏子香”等诗句,皆展现寺观诵经默坐时柏香缭绕的场景。
这种兼具清心功效与山林意趣的香气,天然契合诵经参禅时的空明心境。虽然佛教仪轨推崇旃檀之香,然而山林僧众日常修行多取柏子为用。五代托名陶谷的《清异录》中有一则僧人焚香的故事:
释知足尝曰:“吾身,炉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笺、乳,作梦中戏!”人强之,但摘窗前柏子焚爇,和口者指为“省便珠”。
僧人以五戒十善为香,而不用沉檀等名贵香料,其取窗前柏子焚爇,戏称“省便珠”,既暗合禅宗破除名相的机锋,亦折射出物质局限下的修行智慧。这种返璞归真的用香方式,恰与晚唐赵州、仰山禅师以柏树子譬喻佛法的公案形成互文,共同诠释着“即事而真”的禅家妙谛。
柏子香的道教意涵在唐代发生转型:唐前时期,柏子多被视为仙家服食,《神农本草经》列其为上品,称“久服,令人润泽美色,耳目聪明,不饥不老,轻身延年”。至中晚唐道教传说中,柏子实现了从服食到熏焚的功能转换,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中,柏子成为香料的绝佳替代。唐末刘存希避难山中,“拾柏子焚香,礼敬天师”(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八)。黄观福“好清净,家贫无香,取柏叶柏子焚之”(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卷八),最终成仙而去。如此种种,为柏子香增添了许多神异色彩,柏子香作为代表道教气味的香料,屡见于道教香方,如北宋丁谓所制“太乙宫清远香”,即以柏子为主要香材。董说在《非烟香法》中评点众香,其中对柏子之香的评价是:“如昆仑玄圃,飞天仙人境界也。”正是由于柏子的这种山林清旷、清净悠远的香气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