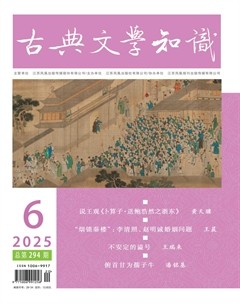在苍茫天地之中,津渡,是个诗意直抵人心的地方。
仔细想来,津渡本身就是江南的一幅泼墨山水,有着诗一般的氛围,如果正值摆渡之时烟雨氤氲,那股诗意也就更浓了。在春潮挟裹雨水涌向河流的时候,荒野渡口空无一人,既没有候客的艄公,也不见赶路的旅人。小舟横卧,水自漂流。岸边幽草生,树上黄鹂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韦应物笔下这七个字,写绝了水墨洇开的津渡夜境。千年烟波里,野渡舟横的旷古苍茫,雨打空舷的寂寥清响,无人独对的孤光自照,都在诗句褶皱处悄然滋生无限情愫,直教后来人披一袭唐诗的蓑衣,便醉倒在津渡的时光跫音里。
我恍然,这“津渡”二字原是诗歌里流淌千年的密码。《说文》轻解“津”字面纱—“水渡也”,那《论语》中“使子路问津焉”的古老问询,恰似在岁月的河面投下一枚青石,涟漪里浮出先民涉水的倒影。再观“渡”字,《说文》谓“济也”,轻轻一划便划破了水天界限,让无数诗魂乘着时空交错的渡船,在“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苍茫里,承载着永恒的乡愁与向往。
古代交通不发达,稍大一点的河流,就没有能力架桥,荒郊野外一汪水,漫无际涯阻去路。行人到此,期盼摆渡。有船桨,有艄公,此岸到彼岸,天堑变通途。津渡,如同陆路“驿站”,成为旅人、行者漫漫征途重要节点,见证人生离合悲欢。旅人行至此处,总要解开缆绳系上心结。山色投西的岔路口,陂塘五月的柳烟中,鸡犬三家的檐角下,这方水码头收藏着无数漂泊者的故事。元朝徐再思曾以一支《梧叶儿》定格永恒的渡头风景:“风雨一帆舟。聚车马关津渡口。”北望羁情如缕,东流湍水似箭,聚散车马碾作关津印痕,风雨孤舟载满人间滋味,恰似时光在粼粼波光里写就的骈俪长句。在枫老荻白的时节,离别在家乡的渡口。从那天起,自那一叶扁舟载走最后一片秋色,天涯便成了游子的掌纹。此后多少回极目凝望,总见王勃的诗行在烟波里沉浮:“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墨痕未干的字句里,宦游人的离觞已化作天地间的愁思,在“与君离别意”的平仄间,激荡着“同是宦游人”的羁旅回声。在这里,“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北宋晏几道《清平乐》)。与恋人分别,自然是“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南宋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渡船繁忙,路中停留,“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汉代《步出城东门》),让人心焦不已。停留时间一长,自起思乡之念,正如汉乐府所言:“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过尽流波,未得鱼中素。月细风尖垂柳渡,梦魂长在分襟处。”(北宋晏几道《蝶恋花》)这时候,一旦河上烟雾弥漫,即使过了渡口,前不见停处,后难见家乡,只让人恨不得“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陆游《浪淘沙》)此情此景,白居易的《长相思》差可比拟,当汴泗双水缠绵千里,终在瓜洲古渡牵住长江衣袖,“吴山点点愁”“月明人倚楼”。这蜿蜒水脉何尝不是人间情思的具象?汩汩清流携着唐时的月色,在“思悠悠,恨悠悠”的平仄里百转千回,将渡口沉淀成永恒的守望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