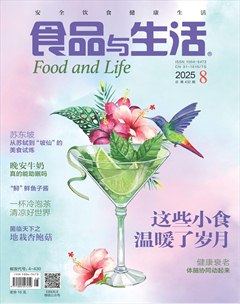公馆改名为弄堂
二十多年前,大头费里尼 (上海作家王海的网名) 和我在上海常德路的一家报社里做同事。我们曾各自骑着“霸伏”助动车,像早起的麻雀,去“捕捉”不同的采访对象;也曾在同一个会场里听新来的领导滔滔不绝地做报告,彼此眨眨眼睛,相继进入“半昏迷”状态。他是小字辈,但我读了他的文章,
特别是他在《海上文坛》发表的文章,就有了点后生可畏的压力。
前段时间,大头费里尼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这样写道一个上海男人:“他一定有着不为我们所知的神秘事业,藉以支撑他钟爱的美食和庞大的社交场面。要么他有缘悭一面的金手指,要么深具你我都熟谙的关于生活、生命的甘苦——只不过他的付之一笑在大多数时间里几乎迷惑了周遭的所有人。”
他写到的这个饭店老板,我有过一面之缘。那家饭店我也去过,不同时空条件下吃过两顿饭,临时身份是某美食榜单的“星探”。举起筷子的时候,不免装模作样,东张西望,弄得服务员相当紧张,以为我是来偷偷在碗里放苍蝇借此敲诈的。最后,菜肴、环境及服务无可挑剔,我给了一个高分。鉴于签过保密协议,这个事情从未跟老板说过。这家饭店就是位于常德路安远路路口的“六号公馆”, 老板姓劳,大家称他“劳老板”或者“劳总”。
上周,一位医生朋友请我吃饭,并发来订餐信息,“鸿祥里”的店名让我感到陌生,但又有一份难以拒绝的亲切,仿佛老家石库门弄堂场景,男女老幼随意出入,宾至如归。
是夜,“跟”着导航一路摸过去,上了几级台阶,进入大堂,迎面看到嵌入墙壁的一个大鱼缸,缸里“悠”哉“游”哉的不是金龙鱼或锦鲤,而是一群比拳头略大的水母。在蓝光的映衬下,水母更显温柔,透明的“裙摆”无比优雅地飘动着,感觉仿佛18世纪法国宫廷夜夜笙歌的再现。我的生物知识相当有限,不过也知道水母对水质要求极其严苛,宠爱这群水母的人,注定要投入高昂的费用,而且在审美上有高于常人的要求。
大堂里还有一台打开的三角钢琴,没人在弹,却不断传出托赛里小夜曲,放在 30 年前,肯定会有人被吓到灵魂出窍。接下来迎宾小姐笑吟吟地将我引向旋转楼梯,这一瞬间,尘封的记忆被激活了,我问:“这里原来是不是叫‘六号公馆’”回答:“是的。”“你们换老板了?”回答:“没有。”
头顶响起爽朗的笑声,劳老板身子趴在黑色大理石护栏上表示欢迎。我依稀记得他曾经的容貌,现在看来岁月没在他脸上留下明显痕迹。我问他为什么要改店名,劳老板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适应当今的消费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怀旧心理。这话没毛病,我表示赞同。
让鸡汤唤醒生蚝的灵魂
饭店的基本格局没变,18 个大包房还在,而且不设最低消费。当晚有一场婚宴,4 张大圆桌设在一个大包房里,还留出了新娘走位的空间,鲜花美酒,彩色气球,一干帅哥美女服务员极具专业精神地将喜庆气氛拉满。
我们哥们儿、姐们儿几个在包房坐定,服务员及时送上冰绿豆汤和果盘,谈笑间,冷菜就上来了。
“鸿祥里” 的菜肴还保留着原有的味觉特征,以上海菜、粤菜为框架,兼容川菜、湘菜的小辣小酸,最能博得年轻人的欢心。
老母鸡汁百叶包、熏鲳鱼、糟味四宝拼盘、甬式酱烤菜心,妥妥的家常风味,是弄堂人家从小吃惯的“老阿奶”味道。深井烧鹅在40年前登陆上海滩,是粤菜大举进入上海时的“先锋”, 曾经风靡一时,成为上海人的味觉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