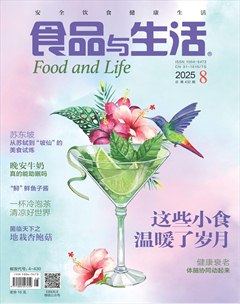管继平
海派作家,书法篆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近些年的汪曾祺几乎也成了“网红”,常听到年轻人提起他或向我打听他的书。一位昔时的文人作家,其作品流传已有半个多世纪,不仅有一部改编版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家喻户晓,而且其小说和散文似乎尤令读者喜欢,至今依然还有人读,还能畅销,关键是还能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那就不简单了,也不仅是“网红”二字可以涵盖也。
有许多文章都把汪曾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也有说是“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其实这些称号都当不得真,说说而已。再譬如像“最后一位闺秀” 之类,我至少读到有六七位著名女史被誉为“最后闺秀”的,究竟谁为“最后” 还真不好说,反正“最后”之后永远还有“最后”。这就像自称是某某艺坛大师的“关门弟子”一般,即便说的是真,但不料老师的“门”并没有“关死”,往往还虚掩着,一旦遇上合适的就又“开”了。所以不管是谁的“关门弟子”,通常我们都会遇上好几位。
不过,汪曾祺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倒确实是真。他的性情,他的文风,以及他的兴趣爱好,无一不透出那种旧式文人的风范。我觉得,文人其实还是有新旧之分的,如果借用孔子的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么前者正好为旧,后者为新。这里所谓的“新”与“旧”,或许可用文人的生存状态来划分,旧式文人的生存状态是休闲型的,读书写作首先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开心;而新式文人的状态则是生产型的,他们的创作总是以提升或教导他人为己任,始终怀有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当然,孔子所说的“今”,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很“古”了。我之所以认为汪曾祺先生属“旧”,也是从他那自在开心的状态来判断的,大概是受家庭的影响吧,汪老的身上一直带有一种“古风”。他的文章颇有画面感,闲适散淡,日常中见出趣味。譬如他在一本自选集的序言中就说,通常“自选集”,应是从大量的作品中选出自认为比较满意的。而自己的作品因数量本来就少,若选得严,就所剩无几了。于是他只能像老太太择菜那样的宽容,有时把择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常言说:拣到篮里的都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这个比喻很家常,但非常贴切。古人云:“文如其人”,我们从他的这种文章风格,基本就能感受到他那闲适从容的文人状态。
因为闲适,旧时的文人作家中擅书能画的不少。书画可以怡情养眼,鲁迅不是有“聊借画图怡倦眼”句么?所以汪曾祺也是,得家庭的熏陶,他儿时就非常喜欢画画和写字。他的祖父是清末的拔贡,功名虽说没有,但诗书自然也是不差的。汪曾祺说他小时候临写的《圭峰碑》《夫子庙堂碑》《圣教序》和小字《麻姑仙坛记》等,都是祖父奖励给他的 “初拓本”。他的父亲名菊生,字淡如,一看就是出自有文化的家庭。汪曾祺曾在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散文中,说他的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擅画写意花卉,又会刻图章,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还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