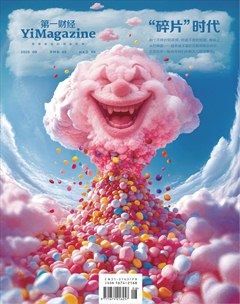36岁的王杨休完产假返岗不久,就遭遇公司关停的噩耗。尽管对生育后的职业困境有所预期,但这场突变还是将她这个新手妈妈措不及防“踢”进了冰冷的就业市场。
在数次面试中,HR几乎无一例外地质疑她能否适应工作强度、是否有足够精力。王杨也坦率地向面试官表示,由于孩子还小,目前她无法接受加班或出差。
身份的转变叠加教培行业下行,这位拥有10年行业经验的前教培机构中层管理者不仅难以匹配到理想的职位,意向公司的平均薪资也比她过去的收入暴跌20%。面对无奈的现实,王杨只能暂时回归家庭,将求职目标调整为收入尚可、时间灵活的兼职,以便在养育与生计之间找到平衡。
在职场,像王杨这样受困于母职的女性员工不在少数。一旦成为“妈妈”,就仿佛自动被削弱了竞争力。如果得不到家庭成员的全力支持,就不得不在个人职业发展和育儿责任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基本职场权益。
今年5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职场妈妈群体存在显著的职业连续性断裂现象,她们中的65.3%做过全职妈妈,56.7%因各种原因重返职场—其中,“减轻经济负担”(21.9%)和“实现自我价值”(19.5%)排在前列。
为了帮助育儿女性摆脱这样的普遍困境,湖北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自今年6月起在全省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鼓励支持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设置“妈妈岗”,并予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
湖北省此举并非首创,广东、湖南、山东、江苏等地从2023年起就已陆续试点推进“妈妈岗”就业政策。上海则将“妈妈岗”的外延进一步扩大。2024年12月,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生育友好岗”就业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支持用人单位将实行弹性工作制、工作方式灵活、工作环境友好的岗位设置为“生育友好岗”,原则上提供给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包括男性。
尽管细则、外延略有不同,且粗看之下,“妈妈岗”确实解决了育儿家庭的痛点,让女性得以兼顾育儿和工作,经过各地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妈妈岗”在实际推行中却引发了诸多争议和诟病。
“妈妈岗”为何屡遭吐槽?
冯兰是江苏一家大学杂志社的编辑,由于行业的特性,加上同事之间非竞争性的工作氛围,她早已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妈妈岗”那样的弹性工作时间和灵活办公地点。但正因为这份“灵活”,自孩子出生,家人就默认她应该承担主要的育儿责任,即便孩子父亲的工作并不繁忙。日复一日的碎片化生活,让冯兰深感“妈妈岗”被吐槽得一点都不冤—单就这极具指向性的名称就值得追问:“有妈妈岗,为什么没有爸爸岗?”
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第三号)》的数据印证了这种失衡:女性每日用于家务劳动、照料家人等的无酬劳动时间平均为3小时29分钟,是男性(1小时52分钟)的近两倍。
支持者认为“妈妈岗”这一称谓符合中国常见的家庭结构和责任分工,能引发社会和招聘市场对全职妈妈再就业的关注,但更多的反对者指出,这种称呼固化了性别分工,强化了一种刻板印象—育儿是妈妈的责任。这让女性本就艰难的职场之路雪上加霜。
5年前,因不放心把孩子交给陌生的育儿嫂,且父母远在外地,蔡子桐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从原公司辞职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她曾在一家中等规模的民企承担工会工作,负责全公司福利发放、活动组织等后勤保障,虽然工作琐碎,但蔡子桐乐在其中,享受将千头万绪的大小事务梳理井然的成就感。
在家育儿期间,蔡子桐发现自己锻炼的能力“当个项目经理也绰绰有余”:婴儿期的吃喝拉撒到学龄期的各种辅导班接送,考验的是流程管理的能力;协调家庭成员的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考验的是团队建设的能力;应对家庭中出现的突发状况并找到最优解则是随机应变和抗压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