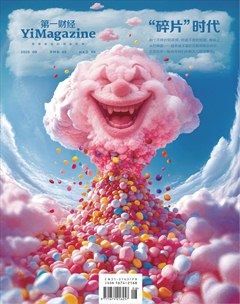编者按:“下沉内容”以惊人的流量和争议性席卷市场,也悄然改变着一群拥有“体面”履历的年轻人的职业轨迹。他们有放弃设计图纸,在直播间灯光下起舞的硕士;有搁置新闻理想,为“爆款”短剧构思情节的记者;也有尚未毕业便扛起摄像机调度团播现场的大学生运镜师。
他们的选择,常被贴上“堕落”标签,遭遇不解甚至质疑。不过,深入故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对高薪的追逐或生存压力下的无奈,也有个体在时代新路径上的主动突围与探索。
他们试图闯入一个只看算法、流量和即时反馈的新规则中,过程自然充满碰撞:收入的不确定性、价值观的撕裂、来自社会和亲友的偏见,以及内心的羞耻感。
故事的背后,是年轻一代对“体面”的重新思考—它可能不再囿于某个公司的光环或稳定的保障,而是关乎经济自主、兴趣落地,以及在这场市场浪潮中对自身价值的定价权。在这个剧烈转型的时代,关于“何以为业”“何以立身”,年轻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设计学硕士做团播这半年
6月,话题“自从做了团播之后,差点忘了以前是干什么的了”在互联网上走红。菜菜也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展示自己截然不同的两面:一边是设计学硕士毕业,另一边是镜头前舞动的团播主播。这条视频很快获得百万播放量,也意外地将她的职业选择推到了父母和亲友面前。
菜菜硕士毕业后在一家设计院工作了7年。这份工作朝九晚五,双休稳定,加班不多,是旁人眼中舒适体面的“好工作”。然而,随着设计行业转型阵痛加剧,菜菜也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七年之痒”。去年年底,她选择从公司离职,寻求转型。今年年初,热爱跳舞的她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家团播机构。
菜菜是个“体验派”,做设计师时,她也会利用业余时间体验其他类型的工作。这一次,她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把团播当作一段独特的人生体验。
以下是菜菜的自述
做团播之前,我其实没怎么看过团播,但我很喜欢跳舞,每周都会去三四次舞室,有时周末一整天都泡在里面。我渴望舞台,而团播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够得着的环境—有灯光师、运镜师、主持人、妆造团队,这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展示机会,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团播机构普遍采用“人海战术”,看重外貌、肢体协调性,以及在镜头前的表现力。当然,头部的团播机构会严格要求主播的身高和体重,普通人很难达到。在这行里,确实存在一些刚刚成年、没有继续上学的年轻人,不过我遇到最多的还是即将毕业或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用一年时间体验团播。从我了解到的真实例子来看,从零开始的人,经历过波折和低谷,差不多会在半年后迎来爆发,因此我给自己的预期也是半年,希望能看到一点成绩,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并没那么简单。
春节期间,我做了第一场直播,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为100人左右,但基本维持在个位数。播了3天,团队就停播了。对一些节奏比较快的公司来说,一个新团3天到一周就能“定生死”,如果观看人数一直在20人以内,基本就宣告失败,公司会果断拆团重组、换模式。
半年里我换了好几次团,每次换团都要经历组团、筹备、练舞、抠动作、妆造、开播和停播。这渐渐变成了一个循环,每组一次新团,都能给人带来新希望,可一开播在线人数还是上不去,如此循环。
新团的筹备时间每次都不固定。我所在的团最短筹备了一周,最长准备了一个半月。每次都是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玩法、不同的团队。半年下来,我直播了22天,一共44场。排练过的舞蹈有四五十,最后上播跳过的,连10首都不到。
时间长了就明白,其实每个团的结局都一样—停播、拆团、重组,只是生命周期长短的区别。现在爆火的团能维持半年以上就算是非常厉害了。等流量过去,他们也要寻求新内容、新模式。
团播绝对是个体力活。每天直播最少要6小时,中间会休息,但开播前需要1到2小时化妆,1到3小时练舞,直播结束后还要复盘,算下来每天至少工作10到11个小时。除此之外,主播每天还要个人单播至少一小时,而且很多时候安排并不紧凑,导致一天在公司待上十几个小时是常事。
我不太习惯的是作息混乱。不同的团开播时间不同,我的作息就得跟着变。每换一个新团,我的整个作息都得重新调整一遍。最累的一个团是晚上九点开播,那时我每天下午四五点到公司,凌晨一点多才能回家,两点多才能睡觉。熬夜带来的疲惫感我常常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缓过来。
外面传团播主播很赚钱,实际上在收入这块,这个行业里的规则很直接:开播才可能有钱,停播就一定没钱。很多公司会在前几个月给主播保底工资,俗称新手保护期,但通常要求一个月直播达到规定时长。等过了这个保护期,主播的收入就完全依赖直播间的流水收入。
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只能拿到基本的练舞补贴,每天100元。即使上播,我播过的几个团也没有粉丝刷过礼物,实际上没有产生过任何效益,也就是说,那点补贴就是全部了。
团播主播就像一台不能停的机器。你拼命往前跑,也不一定有收获;但只要你停下来,就肯定什么都没有。有了上顿没下顿,极其不稳定,导致行业里很多人都会焦虑,能不休息就不休息,都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收入上限高,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实际上,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这里同样遵循残酷的“二八法则”。我了解的一些主播,在直播效果还不错的情况下,一个月也就能拿8000元到1万元;如果效果不好,最低的可能只有1000元。
有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当一个行业火到普通大众都知道,就说明它已经到达高点,增速减缓,红利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