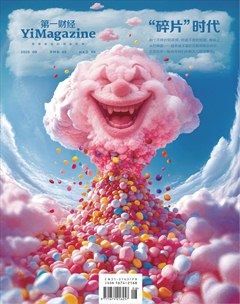Yi:YiMagazine
D:翟东升
01
Yi:最近你听到或看到,觉得最有启发的一个观点是?
D:关于刺激消费,我一开始说福利支出要尽量向年轻人倾斜、向新生儿倾斜,因为年轻人(尤其是20岁之前的年轻人)是“净消费者”,他们不生产只消费,而且消费的转化率最高。财政补贴投入到这一群体后,资金能快速转化为实际的消费需求,然后通过消费乘数效应,带动经济的总消费规模增加,继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补贴的综合转化效果是最好的。
刘世锦老师(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收入,我也觉得有道理。1.7亿农村老人主要是50后、60后群体,特别能吃苦。他们的社会保障非常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积蓄,老了还在城里继续打工,因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的积蓄已经被现代化进程、城市化建设榨干了。
中国农民过上好日子也就大概20年,1980年代、1990年代还可以。建国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工农剪刀差”(注:指农产品价格被压低、工业产品价格被抬高,相当于农业为工业发展“输血”)剥夺了农村、农民、农业,补贴了以北方为主体的工业化地区、城市化地区。中国加入WTO后,和世界达成了一个“交换”,进一步导致了农村的凋敝:中国牺牲自己的农业部门,来换取别国对我们开放他们的工业市场。受益于资本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条件,西方的粮食以非常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导致农民种地挣不到钱,被迫进城打工。而他们打工赚的钱也攒不下来,为了托举下一代进入城市,积蓄都花在了孩子的婚姻、生育和进城迁徙上。
刘主任主张把每个月的农村养老金从2 2 0块钱提升到6 0 0块(我甚至主张第一步先提高到60 0块,将来提高到1000块),这样夫妻俩一共1200块,加上他们有宅基地、农村的自留地,生活成本基本可以覆盖,无需再为生计奔波打工。
如果能让这1.7亿老人加速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就会使得许多必须用人的岗位的工资水平大幅上升,那么青壮年中低层劳动力的收入就会上升,整个消费支出就改善了。
另外从道义上来讲,补偿他们是应该的,这个群体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看不见的巨大牺牲。而且补贴这1.7亿人花不了太多钱,刘老师算下来是70 0 0亿元左右。70 0 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去年的出口退税额(注:国家把企业生产、销售产品时已经交过的税,在产品出口后“退”给企业)是1.9万亿元。所以相当于拿出这笔钱的1/3多去补贴全国的农村老人,拉动中国本土劳动者的收入。
02
Yi:你的新书《制裁与经济战》不久前上市了,你在书中主张从政治逻辑视角探讨经济战,那么在这一研究视角下,有哪些核心观点最值得分享?
D:这本书的起源是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已经在相互制裁,未来甚至有可能陷入到经济战的局面。今天这个时代,大国之间直接开启作战的概率很低,但是互相之间争斗、通过暴力调整相互利益关系和地位的需求非常大,所以只能在经济领域决斗。
这本书也是在跟西方的相关经典对话,或者说是对美国的相关研究进行学术性批判。就是说,不能仅从经济视角来看经济战,还要从政治视角来看。在制裁与经济战里面,政治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在制裁与经济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压力的波动,而不是压力的绝对值。我认为,美国对华的制裁思想比较呆,打的是“添灯油”战术,等煤油灯里的煤油烧掉了再往里倒,火力一直不够旺。打个比方,他想推倒我们,先用一根手指捅了我们一下,再用两根手指,再用一拳、一肘等等,到后边不断加码,但其实都没有推倒我们,因为这个逻辑就是错的。在他们看来,不断提升压力值,最终你会受不了。但是这是一种单边的思维,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有机体,如果冲击它,它是会有反应和调整的。
中国的发力方式以及这种发力方式背后所体现的经济战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同的,要么不动,一旦动就是全面发力,如同中国古代讲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它像太极拳或者大成拳的发力方式,有借力打力。对方是个有机体,要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反应和调整能力,并达成突然的、巨大的力量波动,让这个波动超出这个有机体在短期内的承受力。我们要么不动,要么充分发力,对方受不了就只能暂时妥 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