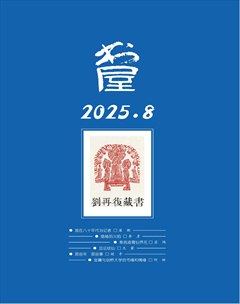“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最不高兴被尊称为“梁老”的梁衡先生,不知不觉已迈入“80后”序列。
此前梁先生一定会反问:“我有那么老吗?!”在他那里,被人称“老”,意味退出历史舞台,行将就木。
从去年开始,梁先生的节奏明显缓了下来。
见到他时,他会感叹几句:“唉,老了,跑不动了,也写不动了!”可自称“写不动”的梁先生仍在写,还于线上、线下讲课。夫人在一旁直摇头:“劝不住!劝不动!”
我知道,一直没有停下脚步的梁先生不服老。可世上谁能不老呢?从1982年他的《晋祠》第一次入选课本,算起来,时间已过去四十三年了,他的文章还在课本里,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梁先生已经八十岁了。
身为记者、作家、学者、官员的梁先生,在我印象里,一直都是那个不怕吃苦、愈挫愈勇、不断求新的上进青年,永远兴致勃勃。
一、铁狮子胡同
梁先生是农家子弟。1946年5月5日,梁先生生于山西南部霍州下马洼村的一个窑洞里。此地因唐太宗曾在此下马而得名。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霍县第三任县长,母亲是农村主妇。父亲忙于公务,母亲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却从不抱怨,家里来人,就说上炕,吃饭。
村里有两座庙,东边是岳飞庙,西边是关帝庙。小学设在岳飞庙里。村里人土炕上生,土窑里长,土堆里爬。家家院里有一个神龛供着土地爷。梁先生能认字时就记住了这副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
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至太原。受父亲影响,他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小学时开始背古诗,最早读的是《千家诗》。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姐姐高中课本里苏轼的《赤壁赋》。中学时,他是语文课代表,给同学们的印象是对语文十分痴迷,读起书来旁若无人,沉醉其中。
1963年夏天,十七岁的梁衡中学毕业,正在菜场打工卖菜时,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全班只他一人考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志愿是学中文,却进了历史档案系,一个对出身要求很高的机要专业。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分城内、西郊两个校区。新闻系、语文系和档案系一年级新生总共加起来也就七十来人。这三个系在城内铁狮子胡同的旧址。
铁狮子胡同的校园,曾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也是鲁迅所写的刘和珍君牺牲的地方。春天里,丁香花和木槿花在校园里绽放,芬芳四溢。
全班二十四人,只有三个女生,年纪最大的同学比他大六岁。这个班后来出了三个部级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梁先生感受到了浓浓的政治氛围。新生入学后,每人都领到一个马扎,开会、听报告时,把马扎一放,整齐而坐,各班唱歌、拉歌。食堂没有凳子,大家吃饭全都站着。学校没有大礼堂,食堂的饭桌推到一边,马扎一坐,就开会。那阵势完全是部队作风,当年陕北公学的传统犹在。
在东四六条38号的校部里(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1949年进京后,有多年办学经验的成仿吾深知校舍的重要性,第一时间在东城区接管了大批房屋,最主要的两处:铁狮子胡同1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和崇礼故居。后者成为华北大学校部),还保留着战争年代的传统,不分办公区和生活区。出了办公室,便能看到锅碗瓢盆和晾晒的衣服,这样的场景在北大、清华是看不到的。
开学典礼上,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南昌起义的吴玉章校长说:“同学们,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了,我向中央请求,派一个年轻的干部来。”早年曾从事地下工作的郭影秋副校长随即抱拳出来。他诗词造诣很深,是明史专家,著有《李定国纪年》……其革命者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这所学校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关注社会与政治,注重实践,注重对学生政治思想觉悟和品德的培养。
拍合影时,同学们一低头,看到了前排八十多岁的校长肩膀上还打着补丁,顿时肃然起敬。成为像他们那样为文为政皆有建树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者,清正朴素,成了梁先生努力的方向。
大学期间,他最爱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历史课,课堂上发言,虽在全班年纪最小,可见地不凡。他还喜欢吹笛子,去王府井书店花几分钱买一张笛子曲谱练习。周日,则学雷锋到学校周围的工地义务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