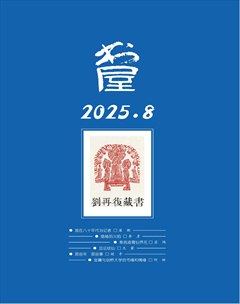对于社会和人文科学而言,西方学者普遍有寻找思想渊源的传统。一个人物、一种现象、一段历史,只要作为对象进入研究领域,学者们就会努力去挖掘这些对象背后的理念源头,作为讨论、解释、证明和得出结论的“思想依据”或“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所著《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以宏大叙事为方法完成的作品,出于自身“逻辑”的考虑,将二十世纪回溯并后延,总共拉长四十年,形成了一部一百四十年的加长版全球世纪经济史。传统惯性使然,德龙在其逻辑背后,寻根了几位重要经济思想家的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思想支撑。阅读这部经济史著作,读者的兴奋点可能会有很多,如为什么要加长四十年,德龙的逻辑是否可信,二十世纪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等等。但深入思想层面去理解这个世纪经济史的形成,更是令人兴致勃勃。毕竟这是历史底层性质的事情,或许可称之为“历史之根”。
一
在宏大叙事逻辑的安排下,德龙将1870年和2010年作为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史的时间起点和终点。他认为,这个“世纪”的人类全部历史可简要归结为经济的历史,全球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人类向理想社会“乌托邦”前行,完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经济大跨越。实现这个大跨越的原因,是北方国家即后称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由技术爆发驱动的工业实验室和层级公司组织的大量涌现,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这里,北方国家、技术、公司和全球化等关键词语,构成了德龙世纪经济史的“北方逻辑”:地域是明确的,技术为发端,经济的强势增长是主线;2010年,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困境,引领全球发展乏力,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逆全球化开始露头,这个弥漫着悲观情绪的年份成了逻辑的尾声。
应当说,德龙宏大叙事下的“北方逻辑”是有史实基础的。
从技术驱动看,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以电的发明为标志,电力得到广泛运用,发电机和各种电气化设备出现,人类工业生产的动力发生巨变。英国是这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美国和德国等迅速跟上,并很快成了革命的中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半导体、计算机、生物等方面的发明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计算机技术、航天、生物技术等的应用获得重大突破,并迅速实现产业化。这次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北方国家,只是美国替代英国成了领头者而已。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突破了人类自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自然限制,“机器替代人”成了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高效率和低成本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形成。
从公司组织看,工业实验室的兴起,技术发明由此开始了向实用产品和服务形态的快速转化;层级公司的大量出现,正好给这种转化提供了高速度、大规模和标准化生产与销售的社会组织体系,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极大地丰富起来;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供大于求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有部分“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由此而来,北方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商品、技术和资本等对外输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全球市场能否进一步有效地扩张,成为北方国家和它们引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个全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应声到来。经济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由经济发达国家商品、技术和资本等的输出带来的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显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一些国家就有过海外扩张和殖民的经历,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些历史遗产演化进入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之中。北方国家主导的这次全球市场一体化,既有旧时掠夺的野蛮遗风,又有新的市场的平等交易原则,汇集成了新的全球经济史最为突出的特征——野蛮遗风体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外的扩张仍然具有强权性质,二十世纪肮脏和血腥关联的事件并不鲜见;平等交易则反映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逐渐增多,并具有某种程度的作用。
无须讳言,作为全球化主导的北方国家,无论是从动因还是从结果判断,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始终是第一位的。仅从结果来看,北方国家商品、技术和资本等的输出畅行无碍,引领了全球经济的世纪性发展,但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北方国家,它们获得的回报巨大无比,“发达经济体”之说,就是此等的全球化带来的。既然做“老大”能够获得超乎寻常的经济好处,北方国家继续当“全球领袖”的愿望就十分强烈。以此来看,这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主导者利益优先的全球化,是混杂着巧取豪夺和市场原则的全球化,还是非主导经济体依附主导者或不平等发展的全球化,更是北方国家,特别是“后起之秀”美国希望长久领头的全球化。
2010年,这样的全球化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发达经济体做了一次世纪性的总清算,这些国家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急剧弱化,利用货币和金融工具转嫁危机又遭遇了强烈的抵抗,主导全球经济大有穷途末路之势;另一方面,代表南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崛起,经济总量取代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全球化中这个极为特殊的因素,不仅无情地挤压了北方国家强取豪夺的利益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外发展遵循的市场平等原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发达经济体如果不改弦更张,便无法取信于其他国家再做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在加长版的“北方逻辑”里,德龙交代了北方国家作为引领者的衰落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则只是轻描淡写地作为“例外”一笔带过,尽管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他的“逻辑”框架之中,中国经济总量和结构强大的优势在这时已经显露无遗。
二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二十世纪有三位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他们是哈耶克、凯恩斯和波兰尼。前两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纪性思想家。他们都聚焦于市场经济,但看法严重对立,一个认同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体系,另一个坚持政府必须干预的市场经济。这样两种大相径庭的思想认知,政府干预是否需要是二者的关键分歧,它们被分别描述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理论学说。
波兰尼在西方国家有不低的声誉,但在中国学界的影响看起来并不大,他的思想未得到多少国内学者一定强度的传播。究其缘由,二十世纪以经济为主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从理论到实践,人们的目光都集聚在“市场”或“市场经济”范围之内——制造理论学说是围绕市场这个中心展开的,从事各类社会交往活动,也是以市场供求和交易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影响强化,活生生地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催化成了几近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任何非“市场化”的社会认知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或是被纳入“市场”中讨论,或是被边缘化。波兰尼的思想,恰恰是超越市场化从整个社会反过来看“市场”的深层思考,它在某种程度上被冷落是不意外的事情。
波兰尼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首先是他的经济历史观。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没有出现过所谓纯粹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人类历史以其自身的悠久长度,已经证明了这种经济体系属于天国而遥不可及,不过是人类理想的另一种乌托邦,绝非能够构建为眼前现实的图景。其次,是他对于社会和市场关系的正名。他认为,社会是包括市场在内的体系,市场仅仅是“嵌入”社会中的一个板块,从属于政治、宗教和各种社会关系;如果说,市场可以不与社会关联交互就能够自我、自由和自动地完美运转,完全是天方夜谭,拥有这样的认知是极其肤浅的。
需要重点谈及的是,波兰尼指出了三种特殊的存在物,是不能自由市场化为一般商品的,它们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或者说,它们本来就不是“经验上”的商品,而只是被人们冠以“商品”之名,出现在市场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里的某种要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它们都有超越一般商品的本源规定:劳动力和人的整体是不可分离的,劳动力的使用和人的使用是一回事;土地和大自然也是不可分离的,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大自然的改变同样是一体化的;货币并非只从属于市场,它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功能,如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物被贮藏、捐赠等。如果这三种存在物可以被自由市场化为一般商品,那么,它们就将归属并依附于自由市场,成为市场供求规律的奴隶,时被闲置,时被滥用,时被抛弃,人的社会尊严就将消失殆尽,大自然的环境可能惨遭毁坏,货币的价值则必定大起大落,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