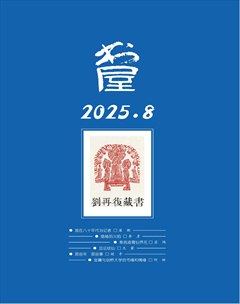《书屋》名字取得好,满溢书香,让我忆及小时候帮外婆晒书的好风景。
隔着半个地球、十二小时时差,e-mail无形无影穿越时空,将《书屋》与我联系在一起,温馨地联系在一起。
文华好脾气,电子邮件中,谈稿件事宜永远是商量的口气,从来没有催过。信末不忘贺节、贺岁,礼数周到。顺便告知,小外孙会站、会走、会跑、会跳、会叫外公了,字里行间都是喜上眉梢,让我读到他的好心情。十年如一日,我们有着不算频繁但是相当温暖的互动。
感觉上,最早在我与《书屋》之间牵线的应当是傅光明。为了老舍先生,我与光明2009年开始的书信往还不但成就了一本书,而且引发了另外一个领域的讨论,那便是莎翁的诗歌与戏剧。2015年5月6日,光明自欧洲返回北京,写了邮件来,标题便是《归来,及〈书屋〉》。信中这样说:“《书屋》刘文华来信,说第六期上将有关于《书信》小书的一个专辑,也不说怎么编的,只说已编好,正在终审,内容‘惊艳’。一笑。还说从第六期起将连载您写夏公的那本书。听了叫人开心!”标准的“光明式”笔锋,一派乐天。信中所提《书信》,便是那本《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2012年3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于“写夏公的那本书”则说来话长。
于是,从一大沓《书屋》杂志中翻检出2015年第六期这一本,封面上竖排“本期主要内容”,赫然见到陈思和教授大文《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那正是陈教授为光明那本《书信》小书写的序文,紧跟着便是董桥先生大文《想起老舍》,收在精致的文集《景泰蓝之夜》里,201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翻开杂志,栏目《旧作新识》的第三篇便是光明的《一信一世界》,谈及清阁先生的晚境。
果真,《人物春秋》栏目只有一篇,便是我由夏公书信起意写的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书名是《书信世界里的夏志清先生》,编辑部使用的标题是《风托霓裳泪沾襟》,想来是文华的手笔,贴切之致。至今,看到这些连载五期不得不中断的文字,我仍然会流泪。因为,这本书写了两次,而2015年我正在写第二稿。原因简单,按照国际出版法,书信的著作权属于写信之人而非收信之人。我引用夏公信中内容,须得到未亡人授权。我写了极客气的信去请教,得到的回答是,将夏公来信扫描给她看,由她决定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在回信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我不在乎夏志清本人,我在乎的是被他月旦的朋友。”书信是一个人写给另外一个人看的文字。不能顺利得到授权,我只得从头改写,将文气流畅、全然夏志清风格的信中文字化作那些信件的内容摘要,纳入这本书的二稿,成为一本文林忆述《尚未尘封的过往》,2016年元月由台北允晨出版社出版。没有得到授权,我只得跟文华说明不得不中止连载的理由,文华展示了他的体谅与会心,悄无声息地中止了连载。然而,十三封信却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印在了“无远弗届”的《书屋》里,成为真正尚未尘封的过往。而那些夏公中文直写、英文横写、意气风发、诙谐有趣、情感真挚的手写信件,则被我装进一个大信封,送给了允晨发行人廖志峰先生,作为我真的曾经拥有这些信件的佐证。时隔多年,我就在想,夏公这位热爱朋友、热爱写信,能把一张圣诞卡写成学术论文的大学问家,寄往世界各地的大量信件,如今大概都成了已经被尘封的过往,或者已经灰飞烟灭,无法闻问了。
倒是董桥先生的大文细说从头,讲清楚了我这样一个人的小故事,为这五期的连载做了清晰、精准的作者介绍,也为傅光明的《书信》小书做了最为独特、最为宽厚、最为犀利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