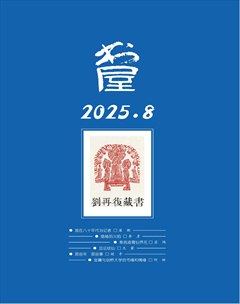背上行囊,独自上路,从长沙出发,杨潇沿着长沙临时大学的足迹,徒步穿越湖南、贵州、云南的二十多个县市,历经一千六百多公里,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做这样的事情?
坊间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很多,较有影响力的是易社强《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鹿桥《未央歌》等,其中交织着汪曾祺、许渊冲、何兆武诸多联大学子的青春记忆,以及后世诸君的推波助澜。“西南联大”不但成了热门话题(与之对应的“西北联大”几乎少有人提及),渐渐被推上民国教育神坛,各类标注着“西南联大”的教材、讲义也都出现在各大书店的书架上。
在众多讲述“西南联大”的书中,杨潇的书别具一格,正因为他的“重走”。八十年前那场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被后世称为一次“文化长征”,相关资料已然翔实,但是用脚一步一步去触摸这段历史,杨潇是第一次。
杨潇,湖南人,资深记者,走南闯北,关注现实。在此前的《子弟》一书中,他重访灾后的北川中学,追踪“北漂一族”的生存状态,关注“公知”的前世今生,其“问题意识”颇具新闻人的味道,对转型中的社会现实格外敏锐。《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之后,杨潇带着对远方的向往,前往美国、埃及、缅甸、德国等十多个国家旅行、访学、短居,去现场观察、采访,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所得与思考。2024年,他推出了新作《可能的世界》,推荐语中有这样的话:“一个年轻记者的新闻实践,带着当时当地的困惑与问题进入事件现场,接近陌生的人群,在思考与写作中还原复杂的时空脉络,寻找可能的答案——‘在线性的时间观里,世界是加速前进的,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往车窗外扔东西,扔掉被这个时代认为过时的东西,以免落伍——我未必相信圆形的时间观,也不打算为“过时”辩护,我只是觉得许多事情都缺乏检视和辩论。’”
“国家转型”是他一直关注的大问题,或许正是这样的问题,驱动着他不停地去行走,去寻找。走到贵州安顺的关岭时,他有这样的思考:
八十年前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年轻学子或许早有类似体验,“一清早爬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只盘算着那天的途程。出发之后眼看着路旁那矮小的路碑的号码增加或者减少,心里面也渐渐地加多了喜悦,像是快完成了每天的任务”。如果说,战争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某些宏大问题的契机,那么徒步本身大约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吧,在一个迷惘的时代,它用方向感明晰、富有节奏的线性前进,推开了胡思乱想与随波逐流,提供了乱世中尤为可贵的惯性,借着这惯性,许多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得以化解。
…… ……
“你知道的,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年轻人总是要证明自己的,”易社强对我说,“我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男人?如何证明我的价值?如何建立我的认同?你可以在文学上一直追溯到中世纪那些出去冒险的年轻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