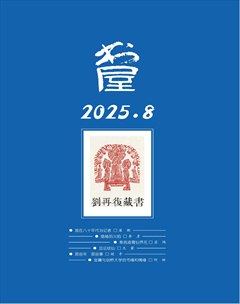最初注意到周辅成(1911—2009)这个名字,是因为关注歌德的中国接受史,在中德文学关系史的现代语境里,周辅成与宗白华合编的《歌德之认识》,是不妨视为一个经典文化符号的,因为其展现了那代知识精英的异域认知的热情和诗哲标志的高度。在书前的编者前言之中,周辅成特别交代了所收文章的来龙去脉:“此集子所收的论文,除谢六逸、华林二先生者外,余均多在北平报纸上所出之歌德逝世百年纪念刊上刊载。以其报上所刊载者不易收存,所以有朋友从上海写信来要我收集成册。我因为写纪念文的诸先生多直接或间接相识,所以断然即担负此工作。我觉我编完此集后,有特别感觉到的,即本集子所收诸先生的文章,实在可表现我国人之吸收西洋思想,并不示弱于日本人。只要我们稍一读日本之研究德国文学的权威(如山岸光宣等)论歌德的著作,再一看此集内的重要的文章,其忠实的研究,表现我国思想界,对于外国文化,颇有深刻了解的能力。”显然,此书的编纂是以周辅成为主的,宗白华只是附署而已;当然参与其事的还有杨丙辰、巴金,周辅成在前言里对他们特别致谢。如果我们考虑到彼时的周辅成弱冠不久,还仅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1933年考为清华的研究生,那么此书的学术史意味就更浓烈些,因为这揭示了在中国现代学术创立期的那种“元气淋漓”状态,即作为第二代学人(1910年前后生人)的学生一代已经可以与第一代学人并驾齐驱、振臂共舞,而周辅成、唐君毅、牟宗三、钱锺书、许思园等无疑都身在其列。
这一切,也都通过一个现代中国知识精英个体的经验而得以呈现。周辅成回忆自己初入清华的情况:“我是从四川闭塞农村出来的出身微贱的土包子,既缺乏君子礼貌,也不懂洋规矩,很难找到像在成都时的同情者(当然也还有我敬重的同学,如乔冠华等),白天有空我只能到图书库去找书看。这个书库,当然比我在重庆时走的新旧书店不同了,大家进书库都是找西文书看。我要特别感谢这个书库,它可以让学生也走进去自己选择书看。这对于我们要掌握某一方面、某一问题的材料,非常方便,而且快,用不着去问师友。这些时间,我遇到了杨丙辰先生,他是北大德文系主任到清华来兼德文课。他喜欢歌德、席勒,并翻译了好几种席勒的名著,我们有几个喜欢德国文学的同学(如季羡林、李长之等)算是和他最接近的人。他不大喜欢跟同事往来,却很喜欢跟同学往来。这个特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走起路来,一件又大又重的狐皮大衣压在身上,使他东倒西歪,很像歌德《浮士德》书上浮士德的插画一样。他似乎受莱辛(Lessing)的话的影响:‘宁愿要无限,不愿要绝对。’他希望中国有一阵狂飙之风,但更希望还要有突进的要求。他口中总说,人不要让低级理智占优胜,干预生活;人应该像浮士德一样,不仅看到‘泰初有行’,还要有一颗真诚向善求真之心,向无穷世界前进。只要能这样,任何魔鬼的妖术也不怕,它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他就凭这点所谓浮士德式主观愿望,拿起一支秃笔向当时以胡适为首的文学阵地进行了进攻。当胡适的周围人正在为他的好朋友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而在各报刊发表纪念文章的时候,他却在《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讲徐志摩远不如歌德天才的文章。这篇文章激怒了他的顶头上司胡适,他任职十几年的德文系主任被解职,在清华的兼课也被取消。当局讲的理由是:他和学生太接近。这真是奇怪的罪名了。”由乡进城,固然已是代入了太多的身份转换的“精神质变”意味;而由川入京,更是由天府之国的乡村闭塞而转为文化首都的开阔宏达,不仅是区域风景的变迁,更有知识、文化、精神、观念视域的系统重置可能。图书馆固然可以“但启新思不为师”,而接触到的人物也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仅有众多同辈学子的相互砥砺,如季羡林、李长之、乔冠华等“天资陈秀”之青年,还有像杨丙辰这样堪称一时之选的导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人物皆为中国现代学术场域里德系背景之知识精英,而由此牵连出的莱辛、歌德等德国诗人和浮士德形象,也都能展示德国文化之精神象征。
周辅成还延伸出了另一条思想史轨迹:“我对歌德与斯宾诺莎有兴趣,使我和当时正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北大贺麟先生比较接近。他是想通过斯宾诺莎最后归到黑格尔,我是想通过斯宾诺莎达到康德。最终,他是理智主义者,哲理智识在行为意识(如道德)之上,就如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所安排的价值表,哲学高于道德、宗教和文艺。我是道德至上论者,不仅行为意识在理论知识之先,而且要说有所谓精神的话,那它也是道德的,或从道德精神推演出去的;这看法,与其说近于康德,毋宁说近于费希特。但我和贺先生思想仍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于英美新黑格尔派哲学的态度。因为这派思想,就是想把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结合在一起。我们都欣赏他们。贺麟先生读的书也广,中外哲学史都很熟,很有真知灼见(insight),我受他的教益和启发,是应当感谢的。”如果说杨丙辰、宗白华都是留德而导致的“德像直见”的影响,那么贺麟的由美至德经历则彰显了另外一条中介取径的路向,此种“德风东渐”的不同向度,展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择取与接受世界性思想资源的重要特征,即既心胸开阔、兼收并蓄,同时也能不拘一格、举一反三,呈现出学习、借鉴与创生同步性维度,深值细究。
当然更重要的,是周辅成在长期生命历程中不得不承受的凄风苦雨和历史寂寞中所坚守的那份“求真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