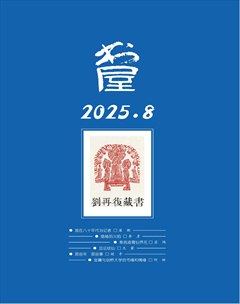一
一部书稿出现在我的书桌上,是张守涛先生的《鲁迅的朋友圈:鲁迅与现代英俊》。“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希望中国出英俊,中国也确实出了很多英俊,当然还需要更多英俊;鲁迅本人是中国的英俊,在他的影响下,很多英俊成长起来。这句话语义丰富,涵盖广,历时长,今天也不过时。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与现代作家的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鲁迅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对鲁迅的传承,兼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有助于丰富对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今天传承鲁迅精神、事业”。本书副题“鲁迅与现代英俊”对论述范围做了限定,二十多位英俊不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等,而是文化人、读书人、知识人,而且偏重鲁迅的专业:文学。
“鲁迅与现代英俊”属于“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的大范围。在中国现代文学家中,交游研究最充分的莫过于鲁迅,《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部分相当详细,对日记中只出现一次的人物的生平事迹都做了介绍。最近还有学者将鲁迅家乡的远亲近邻乃至同时的乡贤都做了梳理,虽然关系较远,也是有价值的资料,因为这些同时代人是鲁迅生活时代的大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读罢序言,就去看目录,却有点疑惑了,为什么将林纾列在第一位?几十年前读文学史著作,林纾是“反派”角色、大批判对象,现在对他温和一些了,肯定他的功绩,读者接受是没问题的。将林纾列为鲁迅一代人所接续文脉的前辈,对他们文化贡献特别是引进西方文学的功绩给予肯定,是很必要的工作。但列在第一位似乎与全书主题略有错位:林纾固然是英俊,但不在鲁迅所“愿”范围内,因为鲁迅还是学生的时候,林纾已经名满天下了。这样排列,可能出于对老前辈的尊重吧。这且按下不表。
二
来不及过多疑惑和反思,就眼睛一亮,心生喜悦,在目录中看到“愿有英俊出中国”一节标题——堪称本书的“书眼”——其副题是“鲁迅与台静农”,用的地方深得我心。因为我收到书稿前不久,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重庆师范大学的老师们一起去重庆,参加了“寻访台静农抗战时期踪迹”的活动。在白沙镇附近山坡上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参观,看着几间刚刚修缮好的教室和院内齐腰高的杂草,想象战乱年代这里的清贫生活和琅琅读书声,台静农就是在这里与朋友们展读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并加题识的。山下的河道在小雨中波光闪闪,让人想象当年台静农从山上走下去,在码头乘船到江津另一个小镇看望他的同乡、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或到重庆参加文化界纪念鲁迅的大会。因为台静农等文化人的传播,陈独秀、鲁迅在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山城的时空交集,让人感慨万千。
台静农是鲁迅居住北京时期培养的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我写过一篇文章《风义师友,斯世同怀:通信中的鲁迅与台静农》,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台静农与鲁迅的亲密关系,归因于他们社会观念相通、文学风格契合和学术理路一致。他们从创立未名社时期相识,到鲁迅逝世,十几年间友情不断加深。……台静农服膺鲁迅的思想和品格,内心深处珍藏着对鲁迅的爱戴和景仰。他在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默默践行鲁迅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理念,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或隐或现透出鲁迅的影响,保持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因为政治斗争的影响,台静农在完成鲁迅未竟的学术事业方面也留下一些缺憾,如我在文章的末尾说到两人通信中讨论的学术计划——我把台静农称为鲁迅的学术传人——介绍了台静农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编纂《中国文学史》讲义的情况:“鲁迅英年早逝,未及完成自己的学术计划。多年后,台静农发愿研究中国文学史。抗日战争结束后,台静农到了台湾,创建台湾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二十多年。他在中文系任教几十年,培养了大量人才,个人著述的重要一项,就是编纂《中国文学史》。因两岸阻隔,直到终老,台静农未能再回大陆。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将讲义整理出版。台静农可能是带着对鲁迅的愧疚离开人世的——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见到《中国文学史》的印行。”他晚年遇到的困难也许比鲁迅遇到的困难更大。鲁迅蛰居上海,困于家累,忙于论辩,欲回图书丰富的北平而不得;台静农则歇脚台岛,形格势禁,缺少参考资料和师友切磋。从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篇幅分配和着力所在,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学术取向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