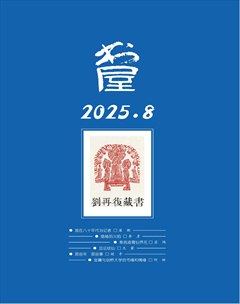一
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浮出近代世界的地表,已经接受了至少四种理论视域的观照:其一是伦理学的。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动态结构围绕伦理实体(及其原则)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代表的是两种在分裂的伦理实体,即家庭与国家内同样具有正当性的伦理诉求。同时正当性也是片面的,双方如果偏执于这种片面性,则冲突不仅无可避免,而且结局只能是双方的同归于尽,“因为在这种死当中,片面的原则被否定了,正义得以最终满足了自身”。其二是法学的。2001年访华的哈贝马斯在《论人权的文化间性》的讲座中抛出了“安提戈涅天条”的概念:安提戈涅相信她为亲人收葬的权利来自“神圣的天条”,非克瑞翁一纸世俗法令所能剥夺。把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之争从法学进路上解读成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冲突,这在西方学术界本是老生常谈,哈贝马斯并没有增加什么,但一些中国学者却从“安提戈涅天条”的说法中得出了自然法在位阶上高于实在法的结论。这当然是过度阐释,因为分析到最后,“安提戈涅天条”只是裹了一层神学糖衣的家庭人伦领域的民间习俗,并非实在法赋予终极正当性的超越法。其三是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主要针对黑格尔伦理学在性别关系上的投影。1974年,伊利格瑞在《他者女人的窥镜》中第一次借用女性视角去挑战黑格尔的男权主义假设,这种假设通过把家庭的特殊性(亲疏有别)伦理与国家的普遍化原则的对立性别化,以达到永恒化这种对立的目的。因此他尽管以辩证法著称,却认为性别差异属于纯粹自然的环节,不涉及历史的时间因素,不会走向辩证的消解(dialectical dissolution)。其四是精神分析的。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分析道,根据定义,对法律的服从不可能是自愿的。当安提戈涅执意以自然法的名义为哥哥收葬时,她真正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她自己的(赴死的)欲望。法律不过是她拿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修辞,这根本上有别于行动的原因或动机。她的动机是借“有尊严的死”证明自己“不愧为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在一个现代版本的《安提戈涅》中,妹妹伊斯墨涅就指责安提戈涅太矫情,她说:“你并不爱我们的哥哥,你爱的是你自己正义的姿势,你想以你的姿势赢得不朽。”
二
检视以上四种解读,笔者遗憾地发现,对这部古典剧作的解读缺失了当时观众的视角:《安提戈涅》对于公元前五世纪四十年代(《安提戈涅》上演的时间)那些享受着“观剧津贴”的希腊观众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个视角的特殊重要性在于,戏剧观赏在古希腊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娱乐活动。作为娱乐产业的现代戏剧生产的是特定的剧场时间,一个日常时间的中断,让观众在其中暂时性地悬搁剧场外的现实问题。所以,人们在走出现代剧场的瞬间,才会有重新回到时间中来的感觉。但古希腊戏剧的功能是模仿和介入现实,而不是从现实中抽身而去。戏剧的剧情发生在神话时代,剧中人物的着装、观念和问题意识却都是当代的。事实上,这种戏剧是以戏剧的形式(利用变形、移位、夸张、浓缩等戏剧手段)将当代政治社会问题搬到舞台上来集中呈现,形同希腊公民的政治观摩课。这也是为什么城邦要用发放观剧津贴的手段把公民吸引到剧场,说到底这是城邦(公民)政治的自我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