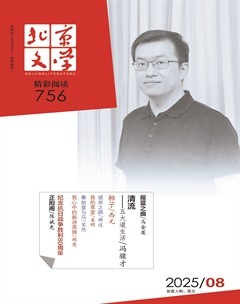这是一篇探讨“权力”伦理的终极指向的小说,作家以冷峻的笔触细写和平年代军队内部的权力异化与伦理困境,军人不再顶着英雄主义的光环,而是血肉之躯,也有幽微人性。当主人公树生将阿牛晋升后的谢礼视为“恩情”,权力的使用披上“施恩”的外衣时,双脚已经在深渊的边缘徘徊……
陆军合成某旅政委姓刘,今年四十八岁,任此职务已四年。平日里,别人一般称呼他为“政委”或“刘政委”。只有零星几次,集团军李政委称呼他为“老刘”。其实,李政委也才比他大四岁。刘政委呢,心里倒是挺认同“老刘”这个称呼的。为什么呢?被称为“老”,一是有尊重的味道,但细细品,这层意思其实可有可无。二是有进步慢的感觉,言语之间,暗示你得抓抓紧,赶快迈过这道职务上的坎儿,否则年龄可不等人。虽然彼此岁数差不多,职务却隔了好几级,终究很别扭,总觉得人家心底里还是瞧不起自己的。第三呢,这里头的滋味只有老刘自己心里清楚。眼看快五十了,中年将过,“春风得意马蹄疾”未曾有过,各种各样青年时有过的憧憬渐行渐远,工作和生活上的“中年压力”倒是越来越沉重,简直有了“逆境”之感,非得拿出“逆流而上”的勇气才行。他觉得自己的世界就像只铁皮罐头盒子,慢慢沉入深海,巨大的压强快要把它挤扁了。怎么办呢?他需要一种东西,足以扛住那如山的重负。有时,他又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在别处,尽管步子万分沉重,可是走着走着,却生出些许喜悦和信心,那塌陷暗淡的世界重又丰满鲜活起来。每到这时,他都会对自己说,莫问希望还是无望,莫问得意还是失意,那些终是身外之物。虽然“老”了,但还要老老实实地走下去,脚下的路才是最真实的。
记忆
几天前,刘政委得知了一件令他很震惊又很困惑的事。该旅合成三营装步九连指导员树生在今年春节前接受了本连一位老兵五百元代金购物卡。上级纪委掌握了线索,已派人进驻旅里调查。按工作组的要求,树生离开连队,临时住在车辆机械仓库的院子里写情况说明材料。
树生是一位让刘政委很牵挂的指导员。八年前,刘政委从某大单位机关到旅政治工作部当主任,树生则是刚从某政治学院毕业的见习排长。刘政委认真研究过干部们的履历,对这个年轻人印象尤其深,因为那所政治学院也是他的母校。年轻人出生的那一年,刘政委从高中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考入了位于长江边的军队大学。记得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就很喜欢大学的名字——某某政治学院。某某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的名字,而政治呢,很神秘又很严肃,仿佛是件很大的事情,两个词合在一起,就很有历史厚重感。多年以后,经历了一些人生风浪的刘政委明白,那个满心好奇的高中生所理解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年,学校里有很多民国时期的老式建筑,有的还是民国政府某部门的办公楼。上课的教室,还有教员的办公室都在一座回字形的三层大楼里头。刘政委所在的学员队,一共不到三十个人,没有女生,甚至就住在那儿。建筑的墙壁很厚,因此窗台也很宽。外墙是暗灰色的水泥,在长年潮湿的环境里,隐隐泛绿,墙根儿处生满湿滑的青苔。回字形大楼中间有一个天井,天井里长满青草,到了休息日,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拔除它们。否则,用不了多久就会杂草丛生无处下脚。楼里很昏暗,走廊也很长很曲折,初来的人很容易转来转去不辨方向。楼梯扶手是木质的,墙壁、天花板都镶有深紫色木条,也就更显昏暗。坚硬的水磨石楼梯台阶和走廊地面在长年踩踏和洗刷下,光亮如镜,有些地方还明显地凹下去,给人强烈的年月痕迹。刘政委的那个班有十个人,住在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里,铺有地板。这地板恐怕最少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早已不平,有结疤的地方鼓出来,踩上去硌脚,而普通木质的地方则被磨得很薄,咯吱咯吱响。另外,存放包裹杂物的库房房门是一座厚达一米的铁门,带有方向盘一样的锁紧装置。在刘政委的记忆里,这座门从来没关过,也锈住了。但它如若关上,恐怕一般的炸药是绝对炸不开的。
四年政治学院生涯给刘政委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不仅是那里的潮热气候、古都风情,还有在四年里所学习过、记下来的东西。当时觉得只是学了一些知识,几十年后回头看,这些东西一点一滴地,却又深深地改变了自己。正因这种无法抹去的感情,使得刘政委对树生这个小了自己十八岁的师弟有了格外的关注。虽然并不经常见面,但刘政委总是利用不多的机会问树生一些问题,打听打听某位教员、某个地点,甚至是学院附近某个小吃店的情况。毕业快三十年了,经历的在职培训不少,可竟然一次也没回过母校。透过树生的回答,刘政委感觉到自己的记忆不再是固定在某个遥远年代的化石,而是在慢慢生长,慢慢真实,和当下的世界衔接起来。可以说,刘政委是看着树生从一个刚毕业的生瓜蛋子排长变成一个游刃有余的老指导员的。
树生,合成三营装步九连指导员,上尉军衔,今年三十岁,在此位置上已干了整整五年。去年秋季,树生参加了军种组织的政治军官比武,取得了拔尖的名次,又一路过关斩将参加了全军比武,得了二等奖。去年年底,旅里给他记二等功一次。如今,他胸前的勋表架上已经挂上了有两条粗红线的黄色方块,这个东西可是大多数人没有的。树生暗自算了一下,全旅胸前能挂这个的不超过五个。他总算松了口气,再有副营职岗位空缺的时候,能跟我比的人不多了吧?
树生和刘政委一样,也是从高中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考进那所政治学院的,进了军校,就算入伍,也就成了准军官。不过,树生入伍时的军队和刘政委入伍时的军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刘政委毕业时去的是驻守在北方的某师,下辖三个团,每个团有三个营,当然,还有一些直属单位。而树生入伍时,已经很少有师,取而代之的是旅。而这些重型合成旅通常下辖九个营,每个营有六个连。所以,在刘政委年轻的时代岗位多,晋升也快,而到了树生的时代,小军官们每向前走一步都不亚于重新参加一次高考。
树生有他自己对母校的记忆。比如他入伍那年,军队已换了新式军装,这个军装体系虽经过几次调整,但风格一直沿用至今。记忆最深刻的是,刘政委当学员的时候,肩上的军衔是一块红板板,而到了树生的时候,变成绿底上有一道横杠,大体相当于没有星星的尉官军衔。还比如,树生那个时代校园中部建起了一座三十层的教学大楼,大理石色的外墙,进入大楼要走上二三十级异常宽大的台阶,简直有点去人民大会堂的感觉。刘政委的记忆里是没有这座很现代的大楼的,那个地方原来是好几排红砖筒子楼,有很多树,把三层小楼遮在后面,一些刚来的年轻教员就住在里头。大三时,刘政委和其他学员帮教员们搬过几次家。那些筒子楼楼道里很暗,钨丝灯泡上油腻腻地挂满油烟,每层共用两间厕所和洗漱间。树生自然不知道,那个民国政府某部门的办公楼还曾经住过自己的师兄们。他学习的时候,这个老建筑的内外早已经过几番装修,门窗屋檐按民国风格用彩漆重新勾画,仿佛修缮一新的故宫。加了许多射灯,楼道里不再那么昏暗,很是明亮。刘政委住过的那层楼改成了院史馆,墙壁雪白,灯火辉煌,庄严气派。楼外竖起几块沧桑巨石,请著名书法家题写文字,用绛红漆填描,更映衬了这座老式建筑的悠久年代感。
此刻,树生正坐在一面白灰剥落的墙壁下。壁下摆了一张旧木桌,简单擦了擦灰尘,也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若不是遇到了这种事情,恐怕还派不上用场。左侧是一扇双层木窗,透过两道略显污涂涂的玻璃,可以看得到外面的高大杨树。此时还是初春,杨树没有发芽,枝杈又尖又细,刺在淡蓝的天空里,随着干硬的风微微摇摆。十几米远钢架车棚下,齐齐地停放着步兵战车、突击车、指挥车、侦察车、医疗车、炊事车……这里位于营区角落里,寂静无人,午后昏白的阳光照射在这些钢铁大家伙上,像一只只酣睡的猛兽。再往远处看,在拉有铁丝网的院墙外面,是一座连一座的土黄色大山,遮住了好大一片天空。一处山顶上有个红白相间的瞭望哨,隐约可以看到玻璃后面站了一个哨兵,很是显眼。收回目光,这里本是个存放机械修理装备的小库房,散发着浓浓的机油味,房间一角还放着润滑油脂桶和修理工具架,只是临时找来了桌子、凳子,和一张旧木板床……
树生
纪委的人来找树生时,他正在参加营里组织的合同战术演练,也完全没想到被问到的事情会和自己有关。直到那张代金购物卡被提及,他才猛然间记起这件事,仿佛在尘封的角落里重拾一个旧物件,尽管也不过发生在两个月前。也在同一瞬间,树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的脑子没再继续转下去,找些开脱的解释,而是坦然地承认了。
现在,树生的眼前摊开一沓稿纸,很多年没用过这东西了。他已经坐在旧桌前想了一个昼夜,只觉天色慢慢变黑,又从漫漫长夜变亮,直到亮得刺眼,没睡觉,也睡不着,没吃饭,也吃不下,一个字也没写下来。很多问题乱糟糟地堆挤在眼前,不知先把哪一个挑出来。
给树生代金购物卡的老兵叫阿牛,入伍第十二年,刚刚由二级上士晋升为一级上士。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社会大环境富裕了,军队士官岗位也多了,所以士官晋升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初级士官,只要能胜任工作,通过技能考核,并且愿意干下去,大多能按部就班晋升。但高级士官要困难一些,尤其是像阿牛这样由二级上士晋升为一级上士,岗位少了,能留下的自然少了。阿牛的老家在滇黔一带山里面,家境不是很好,所以,留下来的意愿就特别强烈。去年秋天,阿牛在熄灯后找过树生一次,提了一大包东西,但被树生退了回来。那一次,树生对阿牛说:“不要想东想西的,好好干就完了。”年底,阿牛顺利晋升了军衔,也留队了。春节前夕,阿牛又找了一次树生,进门之后一句话也不说,往地上扔了这张卡,转身就跑掉了……
树生的记忆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因为从他看到卡落在地上到他弯腰拾起它,这不长的时间里是一段空白,当时的所思所想,何情何感,仿佛是灰色的、空洞的。然后,他捏着这张卡,找了好几处地方,比如说装有各类学习材料的书柜,比如说工作记录本,比如说抽屉,都觉得不太合适,也别扭。最后,他把卡塞到了便装裤兜里,叠好,放进行李箱,又放到了包裹库房。再后来,就渐渐淡忘了,也是刻意去忘记,好似从未发生过。
那么,到底是谁举报了自己呢?是阿牛吗?不太可能。他给我卡,是在他晋升军衔之后,差不多是表达谢意吧?况且,他那么一个憨厚老实的兵,不会干这种事,也没有这个动机。那就是和自己一样等待晋升的人干的吧?自己虽是干了五年,可干了五年的人也不少呢!一个旅那么多连队,有多少连长、指导员瞅着呢!人家凭什么不咬你?可是,别人怎么会知道的呢?那天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难道是有人站在房梁上看到的不成?是阿牛这个家伙说出去的?他是从苦日子里爬出来的山里娃,每一分钱看得都很重。虽是忍痛给了我,可心底里恨我也说不定。不过,这对他也没有好处呀?处理起来,他也跑不掉。或是他喝了酒,跟别人吹了牛?面子上是表达谢意,转过身去,把你看得连猪狗都不如。既然我花了脏钱,你也收了脏钱,那大家就都别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也真是奇怪,过去,树生觉得自己和战友们之间很信任,关系也挺简单,可有了这东西掺和进来之后,猜忌和怀疑便像病毒一样,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
一束柱状阳光透过浑浊的玻璃窗投射在桌面上,无数灰尘在光线里飘来飘去,一只小瓢虫落在稿纸上,在格子上爬来爬去,也不飞走。五年,五年,虽然用嘴说只是上唇与下唇碰了一下,可只有自己才知其中日子的漫长。这是我青春的五年啊!现在,别说晋升了,降职降衔肯定是免不了的。一夜回到刚毕业。八年前我在干什么?那时我还是个刚离开学校,满脑子大道理,傻了吧唧的大学生排长。让我再走一回这八年时光吗?我哪里还有这样的勇气啊!
现在,在连里士兵们的眼里,我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呢?严格来说我不知道,但那些前车之鉴也会让我大致清楚。比如说那些落马的大领导们吧,过去你可能真心信任他们,真心钦佩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正延伸到了你的身边,强有力地改变了你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是,出了事之后,在你的心里,他们又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无比震惊之余,你甚至都没办法把之前的那个人和之后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困惑尴尬之后,记忆便只能把前一个人慢慢抹去,而只留下后一个人。
我呢?大概也要落得如此下场。许多年前,一个文科大学生来到基层,要技术没技术,要军事素质没军事素质,只有一脑袋瓜子理论。怎样才能让大家信任你呢?你得通过行动证明,你是一个好人,一个完美无瑕的人,指导员必须是这样的人才行。否则,谁会听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的命令呢?
过去并未发觉,现在树生越来越觉得,当初自己是带着理念来的,而且是从理念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理念仿佛透明的种子,刚刚撒在心里时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可时间久了,它们就发芽了,而且是先于外面的世界发芽、成长、健壮。他时常感到非常痛苦,与周遭格格不入又不知该如何妥协,似乎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可一旦放弃又倍加痛苦。
刚来这支训练强度很大的陆军连队那会儿,首先折磨的是身体。好在,爹妈给了一副还过得去的身板,母校对体能抓得也紧,树生只用了几个月就达到满分的水平。他也从没把自己当一个排长看,只当是个新兵,有啥活儿往死里干,凡事都要做到最好,只求在战士们心里落下个好名声。
后来当了副连长,当了指导员,树生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声。按照他心里头的理念,这个连队远远不完美,还有很多看不过去的东西。比如,很多人闲下来就没日没夜地打牌,他一直也没学打牌,见了领导也如此。还有,战士找他出去吃饭,他一律不去,觉得这终究是占了士兵的便宜。如此种种,有点“清教徒”的味道,也显得不那么合群。不过,他还是咬紧牙没松口,一直坚持了下来。他的办法是更多的付出,更多的牺牲,做更多的工作,哪怕没有多少回报也想得开。日子久了,大家终会接纳自己。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些年晋升不似有些人那么快,但任谁提起他,都觉得这个人的人品那是绝对没说的。近几年,有的老兵管树生叫“树哥”。树生以为自己的名字里有树,所以叫树哥。其实,老兵本意是觉得树生的做派里很有点鲁迅老爷子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味道,才戏称他为树哥。还有一次,一个来自江浙一带的列兵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你们看咱指导员有没有点像孔老夫子?”站在一旁的四级军士长,来自福建的老梅一拍大腿,道:“你还别说!”
现在呢?我再也没法去面对他们了。我该怎么再对他们说话呢?你自己都不信的事情,还怎么要求别人去做呢?当然,你仍然可以讲大道理,但战士们只会背地里嘲笑你、骂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你要求他们去做的事,你的话变成了一个屁。树生一直觉得,你之所以可以下命令,并且得到执行,首先因为它是对的,是符合道义的。其次,是战士们信任你,从感情上拥护你。再次,才因为它是一道命令,你有下命令的权力。最末,你也可以用利益来打动他们,有时也有用。但这样做迟早会吞噬自己,因为打仗要死人的,一条命可以卖多少钱呢?是无价的。有价的东西换不来无价的东西,只有无价的东西才能换无价的东西。平日里看不出多大差别,但到了生死关头,最末这一条将使一支队伍不堪一击,瞬间垮掉。当然,这种看法和某些人是不大一样的。历史上也确有为了“破城之后,抢掠三日”而打仗的军队,也确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但是,树生觉得孟子的“何必曰利”云云终究是对的,在这一点上绝不能妥协。不仅仅因为它在道义上是正确的,更因为自己正是怀揣着它才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否则,我早就不是现在的我了。
老家
近些年,军队上上下下对这种事儿抓得很紧,有坐牢的,有处分的,有免职的,有降职降衔的,有大领导,也有小干部。每过一段不长的日子,就能听到通报说,某某某被调查了,某某某被判刑了。当然,还有一些小道消息,说某某某是开会时被带走的,某某某被纪委找去谈话就没再回来。还有发生在身边的例子。去年夏天,旅政治部主任被免职了,原因是“外出吃饭时授意下属买单,接受下属高档酒水”。这个主任树生接触过,眼睛亮亮的,研究材料的时候,思路飞快,开会交代工作时,颇有点神采飞扬的感觉。可现在,在营区里再也见不到他了,听说降了两级,转业了。每次听闻这些,树生都很受震动,不觉间生出一种“惶惶”之感。
可现在,当树生坐在这间满是机油味的小房间里面壁思过时,他非常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心中有了如此“惶惶”之感,却仍然重蹈覆辙?他反复回想记忆里那个接近于“断片”的瞬间,自己怎么就弯腰拾起了那张卡?怎么就塞进了便衣口袋?当时在想什么?“惶惶”之感哪里去了呢?他竭尽全力去恢复那个瞬间,走进当时那个自己的内心世界。困惑、悔恨、恼怒、失望等等情绪搅在一起,仿佛隔着厚厚的时间牢笼,打量一个很陌生的人。
思来想去没有结果,或者说没有什么深刻的结果,都是一些人云亦云的说法,不提也罢。不过,有一个结局倒是越来越清楚。这次,自己恐怕逃不过降职降衔,然后走人的结局。这是一个树生不能面对的结局。他不敢看前方,于是,思绪便像被堤坝拦住的洪水一样回到过去。
树生出生在东北一个重工业城市,2000年上小学,也差不多从那时起开始有了对这个世界的记忆。当然,这记忆是一种类似于整体的感觉,而不是支离破碎的零星记忆,比如冬天里舌头粘在铁管子上了,比如手掌被大杨树上的洋辣子蜇了。那是一座建在平原上的城市,面积和国内任何一个超级大都市相比都不逊色,只是人口没那么多。毕竟,那里冬天很冷,给南方人一种强烈的异乡之感。因为四周是平原,所以它一直在扩张。过去,城郊流过一条河,而现在,那条河已变成了城市内河,把城区一分两半。树生上初中的时候,市政府由城中心搬到了河南岸,这样,在一片荒地之上一下子就有了高楼大厦。
上了大学,树生便也离开了家,离开了那座城市,如今已经十二年。它给树生留下的印象是一幅图景:那是在深冬里,天空湛蓝,冰冷的空气里有雾气有灰尘,阳光像老照片一样有很强的颗粒感。面前有一条很宽的马路,从这边向那边望,像望过一条很宽的河。马路两旁有密密的大楼,遮天蔽日,带钢铁框架和玻璃外壳,泛着早晨清冷的阳光。这条马路从城里而来,延伸到远方,一直消失在地平线。路边的杨树下堆着连绵不绝的积雪,雪上落着尘土,还有踩踏上去的黑色脚印。远处,不知是哪一家工厂的红砖大烟囱里冒出浓浓的雪白色烟柱,映在碧蓝的晴空里,格外醒目刺眼。这幅图景里没有多少车,也没有多少人,到处空荡荡的,透着一丝陌生,一丝荒凉。
如果春节能休假探家,树生便离开连队,去父亲那里住段日子。当人们还在新年里熬夜并且沉睡不起时,他会早早起床,站在路边看看离开多年的故乡。这幅图景便是他看到的样子,并且一直没变。
树生父亲家在城的西边,那里曾是重工业区。不过,在树生有记忆之后,便没有多少工厂,也没有多少棚户区,大多建起了高楼,变成了居民区。他的爷爷过去是那里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干了一辈子,在树生的记忆里他已经是个退休的老头了。隐约记得有一次幼儿园放学,爷爷接他回家,路过一个淡绿色的大铁门。爷爷和传达室的人高声打了招呼,说笑几句,领着树生进了围墙。那是个夏天,太阳很热很低,尘土很大。院墙里有林阴路,有花园,有凉亭,还有一排连一排的水泥色钢结构厂房。不过院子里没有一个人,静悄悄的,厂房的玻璃碎了,花园里有杂草,偶尔见到几只狸花猫躺在木条座椅上晒太阳,一点也不怕人。爷爷领着树生走了一大圈,那是个很大的工厂,出门前回过头,对他说:“小洋洋,我在这儿上班。”小洋洋是树生的小名。于是他就记住了,爷爷曾经是个工人,在城西边的工厂里上了一辈子班。后面,那个工厂拆掉了,原址起了一座宜家和一座集吃喝玩乐购物于一体的巨型商贸中心。近几年,由于电商兴起,连这个当年最时髦的商贸中心也渐渐冷清起来。
树生隐约记得小时候自己家和爷爷家住一块儿,是在一片平房里头。那里布满蛛网一样的煤渣小路,小院子里几家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用红砖垒的小菜园里还种有大葱和豆角一类青菜。后来,那片棚户区拆了,盖起了小区。自己家和爷爷家作为回迁户,住进了楼房。后来,父亲做生意挣了些钱,在河南岸新开发的社区里买了更大的房子,便和爷爷离得远了。每当树生回到童年时待过的地方,总有些不辨方位之感。儿时模模糊糊记忆里的所有地理坐标都不见了,比如说挤在一起的红砖平房,比如一个老太太开的小卖部,比如一家录像厅,比如一家春饼店,比如一家清真馅饼店……
爷爷和父亲简直可以说是两类人。爷爷话不多,几乎没听过他抱怨过什么,走路时低着头,似乎是在看路上有什么可以换钱的东西,时常捡回来一些螺丝、电线、角钢等金属品,扔在屋角一只木头箱子里。他的手关节很大,指甲油黑油黑,洗手时脸盆里的水上面会浮出厚厚一层灰色油脂。树生不知爷爷在想些什么,他说话很谨慎,不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做什么评价。在爷爷退休前几年和退休后的一些年里,他还在街上卖过将近十年时间烧烤。不怎么高级,是一只带篷子的铁皮双轮车子,上面带着煤气罐、电瓶、油桶和调料瓶等家伙什儿。车身上拉了条红绸布,上面用白漆喷着“刘记烤面筋”几个字。这条红绸布是爷爷从工厂拿回来的,过去大概是横幅一类的东西。爷爷六十五岁那年,在街上和一个中年汉子打过一仗,用铁扳手把对方的胳膊砸折了,自己的头上也缝了二十多针。来龙去脉一句话说不清楚,还是为了保护他的“刘记烤面筋”车子。
父亲是另外一种人,怎么形容呢?是个典型的这个城市里的“老爷们儿”。整天嘴里骂骂咧咧的,上到玉皇大帝,下到草芥蝼蚁;外到世界形势,内到吃喝拉撒,没有什么是他不骂的。他不信什么,也别想让他信什么。在他眼里,信仰啊,理想啊,未来啊,蓝图啊,等等所有现在不给你,现在到不了手,得将来才能付款,将来才能实现的东西,统统都是糊弄人的。树生觉得,这可能和父亲看到的、经历过的有关吧,黑格尔不是说过嘛,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事儿。爷爷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临退休前几年,工厂才没有的。父亲呢,当过十二年工人,三十岁时厂子没了,开始靠一膀子力气谋生计。扛过麻袋也搬过砖,修过汽车也修过鞋,摆过摊子也卖过肉,快五十岁时,开始给某个外国大品牌做代理,工作算是固定下来了。主要是跑单位机关、学校企业,把这种东西推销出去,提成虽然不高,但好在收入很稳定,不用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现在,父亲也马上六十了,买了房子,有了些积蓄,孩子也有稳定的工作,想休息了。他买了几对核桃,一条大金刚手串,戴着劳保手套搓,没事用猪鬃刷子刷,盼着早点儿把手头的活儿都了了,一大早起来可以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揉核桃。至于将来得了大病怎么办呢?他倒很豁达,对树生说:“到时我自己拔管子,绝不连累你。”
爷爷像个“狠人”,父亲更像个“浑人”(父亲也觉得自己是个浑人)。如今,在这座北方曾经的重工业城市里,这两种人是越来越少了。他们都老了,退出了历史舞台,蒸腾在这座城市血管里洪荒的、粗俗的、野蛮的气息也越来越淡了。父亲那些絮絮叨叨的话,树生能听进去,但打心里不认同。他不反驳,但也在心里说:“你瞪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世界不是你过去的那个世界了,别再翻老皇历了,你那一套东西不管用了。”他也知道,想在父亲那样的人的心里树起什么崇高的、宏大的、坚固的东西是很难的,就像在沙子上建一座高塔。况且,无论如何,是父亲把自己养大的,你现在说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可当年的苦日子还不是靠他撑过来的吗?你可以指责他卖肉时缺斤短两,但这缺斤短两的钱却用来买你早晨喝的牛奶。每每想起这些,树生的心里就会泛起一阵永远无法抹去的刺痛。父亲的话,耐下心来多听听没坏处,省得头脑发热。总之,这么些年,树生一直抱着“你絮叨你的,我坚持我的”的态度来与父亲相处,上了大学之后就更是如此。
回去吗?回到那座我出生的城市去。树生在想。可是,我不想回去。那是个大城市,很多异乡人都愿意去,愿意靠着拼搏留在那儿。可我不想。那是一座让我的父亲一辈子动荡不安的城市,这动荡不安的感觉也种在了我的心里。我愿意漂泊在外面,远远地看着故乡,尽管在外面也未必就生活得更好。那座城市造就了无数四海为家的儿女。
更重要的是,当我回去了,就等于退回到了父亲那里。我已经离开家,离开他十二年。我已经艰难地向着与他相反的方向走了很远,我不想再走回到他那里去。父亲的世界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一般的世界。除非他自己愿意,否则谁也救不了他,也没有资格去救他。事实的真相更可能是,他救了我们这后一代人。我这个儿子只是踩着他的肩膀才走出了无底沼泽,而他则永远留在了过去。
当我一败涂地、垂头丧气地回到父亲身边,我要对他说点什么呢?难道我要说:“你是对的,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你看待人的方式是对的,而我,是错的。是的,你说得对——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肉就那么一点点,你要是不张开獠牙,你要是不拼命,肉就被别的人吃进肚子,而你和你的家人就得饿死。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没办法呀,我的儿子。啥也别信,只信能到手的东西。那些让你信点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想骗走你的血汗钱。他告诉你,先干一年半载,到时给你更多。可你看着吧,到时他早就脚底抹油没影了。嘿嘿,这世界没好人,这世界就不是让好人活的,好人都死绝了。”
想着想着,树生好像又回到了弯腰拾起代金购物卡的瞬间。原本以为那个瞬间又晦暗,又空无一物。现在,当他再一次站到了那里,发现背后竟是父亲的世界……
终于,树生觉得杂乱无章的思绪有了起点,于是他在稿纸上写下:“本人树生,男,1994年生,2012年从地方高中考入某某政治学院,同年入伍。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我的爷爷也是工人。我的家境并不好,能够一路走到今天不容易。我本应加倍珍惜,可是……”
老刘
距离树生盯着的这块墙壁1500米处,在山脚下,有一座灰白色办公楼。刘政委坐在三楼左侧第一间办公室里的褐色桌子后面。眼前是两张单人沙发,墙壁上挂着3D立体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此时,浓郁厚重的夕阳正打在上面,于是,高原山脉便在平原大海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望过去,就好像你真的变成了一只雄鹰,飞翔在高空,俯视着人间的山河大地。
他的办公室极为简单,像清澈的湖水,一眼便望到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