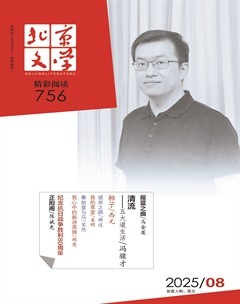“羊”在文学世界中承载了丰富的意象内涵,是祭祀的“三牲六畜”之一,也常被赋予宗教象征意义,这种复杂性是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年轻诗人刘博文(姆斯)以“羊”为其小说创作的开局,展现他诗歌之外的另一副笔墨,为读者带来一篇充满异托邦色彩的寓言故事。
他杀了三年的羊,今天是他第一次下不了手。
三年前,父亲把属于他们家的四季营地交给他。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他第一次独自一人站在夏草场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青翠的绿,偶尔点缀几株紫花苜蓿,闻起来就汁多、香甜。有时他也俯下身,啃一口,他想知道他赖以为生的伙伴们是怎么生活的。他喜欢和它们一起生活。
父亲死后,他就要独自照顾这些动物。虽然才十五岁,他已经可以娴熟地给它们剃毛,在暴雨天赶它们回到棚里,秋冬时节领着它们浩浩荡荡地迁至山谷的冬牧场,并自己制作备用饲料,也就是按一定配比将干草、燕麦、大麦、夏天留存的巨菌草和绿叶蔬菜混起来,喂给它们,有时也不耐烦,一个一个一拍屁股就赶到牧场边缘的常绿灌木丛让它们自己啃硬的叶子。那些羊笨拙,不知道挑空子钻,总是在狭窄的地方突来突去,叶子没吃到多少,一身的毛都挂在了灌木丛的细枝上。放眼望去白花花的一片,好像整个灌木都变成了羊。要是羊可以这样繁殖就好了,他想,不过回头还要骂一句,笨畜生。被钩下来的毛太散,收集起来麻烦,收集好了也难用,但每次掉毛的地方露出地图般的灰粉色皮肉时,他总忍不住轻轻抚摸。孩子,别怕了,孩子,你是那样温暖。
他对所有羊都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喜爱,近乎怜惜,尤其是在深知这些羊小部分会被卖出去,大多数都要经由他的手去到另一个地方,而留在凡间的皮肉将让他们家吃饱穿暖时。于是他想,他一定要对这些羊好好的,让它们生前尽量无痛,死时也尽量无痛。但唯独对其中一只公羊,他不敢施加自己的怜悯,他只有敬畏。
那是他们家赖以生存的公羊,这只公羊是在他六岁时买回的,当时还是一只小羊崽,现在已长成一头雄壮的公羊,两只粗大的角向后卷去,又猛然向前收束成匕首般的尖角,使你站在它面前都不寒而栗。但他不惧怕这只公羊,他们已经成为家人,同吃同住。千百只其他的羊都在羊圈里过着肮脏的集体生活,偶尔有一两只在山间迷失,都无关紧要;但这只公羊必须单独生活在他们家木屋旁的副房里,与客厅只隔着一扇低矮的木门。
金和村的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格局。
在这个村里,斗羊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每家都会精心培育出一只最好的公羊,给它喂额外的吃食,保证它在冬天不会生病,固定时间给它清理毛发。若是常胜羊,剪下来的羊毛穿在身上都是一种威风。不过这只羊也是最苦的,因为家里的父亲(或儿子,若父亲过于年迈)会带着它去山林里训练。
金和村傍山而建,山上有一片片高大的白桦林,每棵白桦树都粗壮而笔挺。不知是因为它们过于笔直,排列得过于整齐、疏淡而肃穆,还是因为白桦树的树干总是斑驳,而且覆满错落的树眼,于是冷灰、蛾白、幽黑交杂,就算在郁郁葱葱的夏天也俨然一幅冬天的景象。可是在靠近村落处的林子里,能看到浅色树干上刷的一道道镰刀状的红色油漆——为了模拟每只斗羊被漆红的角——这瞬间让树干群营造出的冬天氛围增添了一抹杀气,好像结霜的皮肤上划开裂口,留着无法凝结的血。村里用来战斗的公羊,就是在这里训练的。
一大清早,就能看见三两个村民牵着懒散的公羊徘徊在树林边缘,等到找好各自的树,他们就会牵着穿入羊角的绳子,把羊领到十几米远的地方,时刻保持羊头向着指定的漆红的桦树。此时训练有素的羊早已会在眼中生出可怖的火花,牙齿微微打战,就等着主人与它退到一定位置后猛地向前冲去,在接近树的刹那主人会在它的屁股上打一记响亮的皮鞭。就这样,它的角会狠狠撞进桦树的红色部位,好像要嵌入敌人的胸膛,一树的鸟都猛然惊起,朝天空飞去,这是金和村报早时的方式。红色的油漆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中脱落,村民便刷上新的,和旧的一样血红,这样羊就有无穷无尽的敌人要刺破,它们的一生都在与红色对抗。
他的父亲是训练公羊的好手,他们家的公羊在父亲手上训练出了魔鬼般的体魄和冲劲。别家的羊一般要撞三四天才能将桦树的漆撞到几近脱落,他们家的羊只需要一次训练就可以。为此,父亲无比自豪。凭借这只羊,父亲成了村里斗羊大赛的常胜将军。他记得每次父亲胜利后,都会赢回敌手家的一只羊羔(偶尔是一只母羊),当晚他们一家就能喝到鲜美的羊汤。而母亲会把小羊羔的头捧在自己的头前吓唬他,逗他玩,时而唬得他惊叫声连连。父亲就会轻轻地怪道,嗳,行啦行啦,别吓着孩子了。但这是独属于他和母亲之间的游戏,屡试不爽,乐此不疲。
而这些美丽的时刻在他跟着父亲学习训羊时又都显得荒谬而残酷。与父亲不同,每次他看到自家公羊眼中闪着恐怖的光,他看到的不是英勇,不是腾腾杀气,而是恐惧,恐惧自己如果输了这一局将受到难以忍受的皮肉之痛。他亲眼看过父亲曾怎样一鞭又一鞭地抽在这只尚未成为常胜将军的公羊的屁股上,那本来肥厚的脂肪团被抽得血流不止,这一块紫了起来,那一块瘪了下去,于是羊流下痛苦的眼泪。这一切他都记得。在他十四岁的一天,父亲第一次让他训练公羊。于是他铆足浑身的劲,用细弱的手臂扯着羊角向前冲刺。快撞上树干时犹犹豫豫地在它屁股上打了一鞭子,羊就这么轻轻地碰上了树,一块红漆也没有撞落。父亲突然脸色阴郁下来,走上前夺过他手上的鞭子,重重地挞了一下地面,把羊惊得一颤,也把他吓得杵在原地,好像这一鞭抽在了他心上。
自中学以来,他就对这种野蛮的活动表现出反感。
他是全家唯一一个考上中学的人,就算考了两次,入学比大家都晚一年,他还是全家的骄傲。开学前一天晚上,父母特意宰杀了那只公羊的小羊崽,准备了一桌香喷喷的菜。他记得那碗羊汤格外鲜美,他喝得一点都不剩,包括他平时不怎么吃的葱花,一些细小的沉在碗底的碎骨,和尚有腥味的血块与骨髓。看到这些血块,他就知道这只羊一定是父亲杀的,因为只有使用窒息法才会让羊在烹饪后还残留那么多血块。于是他又不禁打了一个哆嗦,他想起每次父亲杀羊,都会先把羊的四肢绑起来,让它侧躺,再在它的鼻子和嘴上贴好湿纸,羊就会窒息而死。不过死前会挣扎好一阵子,在地上剧烈地扭动。虽然羊的鼻孔不再通气,但他能感觉到那个鼻腔中有沙尘冲撞。因为羊的嘴巴被严严实实地封闭,所以无法嚎叫,发出恐怖的咩的颤音,而他似乎能听到某种暴力的摩擦与振动在羊的声带发生。那振动类似于闷雷,或一些徒劳的音乐,类似于,拉一把弦被摁紧的小提琴。一只羊窒息死的时候,对于他父亲这种并不敏感的人来说,是悄无声息,令人安宁的,唯有时常绑得不够紧的四肢触地,还有那些在痛苦中扭动的肌肉,会在泥地上画出生命最后的印迹。他父亲有时会在这一切结束后去看一眼,感叹道,力气还挺大,随后把羊拖到别处处理。一夜雨后,这印迹也就没了。
他不喜欢这样。他不喜欢这种冰冷,这种看似无声其实震耳欲聋的挣扎,好像脚下的地狱发出隆隆声响,隔着一层厚厚的大地,他的双脚却全感受到了。而他总觉得,羊那双门闩般横着的瞳孔,好像就藏有通往地狱的路。所以他选择放血杀羊。
这种方法简单快捷。只要用尖刀在羊颈部靠近咽喉处横切开皮肤、肌肉、颈动脉和气管就行,然后柱状的血就会喷涌而出,羊还没来得及痛苦、挣扎,还没来得及把眼中的门闩转成竖直状态,就已经死了。那些鲜红像满山的木棉花在春天的暴风中散下,他感到温暖,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生命逐渐弥散在屠宰棚里,然后消散于更广大的空气中。这种红,他想,不是憋屈的,不是痛苦的,而是绚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