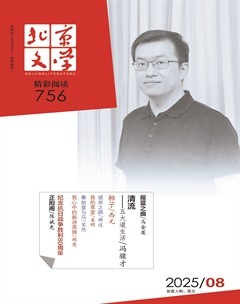一
草堂当然不是我的,是杜甫先生的。
但是此刻,2025年2月4日,农历乙巳年大年初七,“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的日子,在离杜甫草堂只有一公里的我的家中,书页间蓦然出现的“草堂”字样,电光石火般打通任督二脉,我急急地放下手头的书卷,束手恭立,虔诚西望,望向或许正在进行人日纪念活动的草堂,也望向我曾经的工作地、寄居地、我的青春过往。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多少年以来,杜甫的名字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启蒙和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他的文化程度有多么堪忧。因此,杜甫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都受惠于他,他也当得起“诗圣”的称号。尽管一代代学人和作家艺术家对杜甫、杜诗甚至杜甫精神持久不辍地进行着考证、研究和书写,我也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杜甫与我本人——恒河沙数之一粒、芸芸众生之一员,有任何关联。我是如此之渺小,故我有自知之明,任何企图通过攀附诗圣来显摆或者证明自己的方式,都是荒唐可笑的。
当然,人的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此刻,当我写下“我的草堂”四个字,你很难想象我的激动,那是一种立春次日万物欣然、触目有灵的雀跃和心得,我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借喻和互文:草堂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就像锦水春风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咱们的老乡苏东坡不是早就说过吗,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就是主人;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即为主人,心得即为拥有。
公元759年冬天,饱受“安史之乱”羁绊的杜甫,携一家六口,自甘肃同谷县出发,经蜀道,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到成都。杜甫祖上都是官宦世家,家境却每况愈下,到他祖父杜审言这一辈,官阶已经很小了,杜甫无法像高适一样靠父辈荫庇“保送”进体制内为官,加之杜甫年轻时又没有考中科举,好不易通过献赋获得了一个小官,“安史之乱”中由于忠于皇帝得以继续为官,却因为说了皇帝不想听的话被贬,俸禄微薄,无以养家糊口,只好辞官漂泊。洛阳、华州、秦州、同谷,“一岁四行役”,始终找不到可以造屋落脚的地方,他的目光穿越莽莽秦岭,终于落到了一片清幽、宁静之地——成都。成都以极大的宽容和友善收留了杜甫,他得以在此造草堂、修园林。草堂所需土地,为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批准使用,而园中所种松、楠、竹及其他植物,均为杜甫以写信或赠诗等方式向其他官员朋友索讨而来。修筑草堂的“主体工程”耗时好几个月,此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改扩建”。在这里杜甫留下了240 来首诗,总基调都是欢快明亮的,即便是索要财物,也毫不惭愧,甚至显得理直气壮,看起来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他还是很有底气的,也恰恰是这些资助他的文朋诗友,与杜甫共同构建起了一方名垂千古的文化圣地:杜甫草堂。成都是文化名城,城中古迹众多,但是没有多少争议的“文化地标”,武侯祠算一个,杜甫草堂也要算一个。所以这一方草堂,不仅给唐朝的杜甫一家提供了一个庇身之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诗歌、给成都历史,增加了一段弥足珍贵的传奇。
我是1992年2月来到成都的,赤手空拳,身无长物,百般困顿,好在当年12月左右,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入职了一家经济类报社。这个报社刚刚从重庆搬到成都来,发展势头很好,正在大规模招兵买马。好巧不巧,报社办公地址,就在草堂北门的斜对面,中间只隔一条小小的马路,我记得当时报社用的信封,地址写的就是“草堂北门对面某某报”。更巧的是,这家报社先后招入的多位员工,都是当时,甚至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有一点名气的诗人,比如柏桦、肖开愚、孙文波等等。记得那年冬天成都下了很大的雪,我是在办公室看到雪花飞舞起来的,平生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雪,少年的心骚动不已,早就无心上班了。部门主任也是性情中人,他做出决定:集体翘班去玩雪!去哪里玩雪?去草堂玩雪!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创意!杜甫是我们的邻居,下大雪了,我们不上班了,去找他老人家玩雪!如果他老人家真的还在,会不会把我们写进诗中?“肯与小子耍冰雪,隔篱呼取尽余杯”,他一定会端着一杯酒慈爱地看着我们玩,而我呢,会不会裹一个雪球掷向他的酒杯,嗔骂之下他会不会又写“邻家群童欺我老无力,敢教雪球夺杯酒”?杜公成天苦兮兮的,但是在这样的雪景之下,一定是有清词丽句满溢而出的,你看,在他亲植的松针上,天地精灵将坠不坠盈盈欲语,可不就是浣花溪上那涟漪的余波光影吗?你看,那俏丽的蜡梅、红梅被雪花一吻再吻银装素裹,可不就是冷艳凝香一枝春吗?而少陵草堂的茅顶,早已覆上了厚厚一层雪,不是爱“雪”即肯死,只恐“雪化”老想催——杜公会不会担心他的茅屋为大雪压垮?想来是不会的,这雪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风雅是足够的,离灾患那还远着呢,毕竟这是南方的雪,比不得老杜心心念念的老家河南的大雪……
那一年我二十出头,正是青葱好年华,办公室的同事也多是三四十岁,都有大把年华可供抛掷,我们打雪仗,我们摇树枝,我们高声喧哗,我们朗声诵诗,我们奔跑或者驻足,我们放眼或者凝视,我们像诗人一样蹙眉显出深沉的样子,我们像疯子一样哈哈大笑却并没有笑的充足理由……这是1992年的冬天,这一年成都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再一次看到这样的大雪,已经是十多年之后的2006年了。
草堂观雪的情景多年来反复出现在我梦境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清冽和圣洁,就是一个大大的寓言,或者就是杜公的叮嘱,命定我成为那个永远无法离开他的人。我知道自己是有愧于草堂的。在观雪的几个月前,那时我还没有在草堂边上的报社上班,有一天重庆来了几个朋友,加上成都的几个朋友,一群人中午聚餐,喝了点酒,餐毕一起去草堂喝茶。那是个周末,草堂茶馆人很多,我们催了好几次才给我们上茶具,是盖碗茶,上面是盖,中间是杯,下面是托。盖碗茶是当年成都茶馆的标配,即便是今天,但凡是露天茶馆,比如最负盛名的鹤鸣茶馆等地儿,多半还是使用盖碗茶。分茶具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手抖,一个茶盖掉地下,摔烂了。老板似乎很忌讳,态度不好,大声说要赔几块钱。有朋友就说,只坏了一个盖,哪里需要那么多钱?一副完整的茶具也就几块钱。老板急了,说你把盖子摔坏了,那个茶具就废了,当然要赔整副茶具的钱。这个时候我出现了,刚才说了,我们是喝了点酒的,酒壮人胆,我不由分说地操起了那余下的茶杯和茶托,狠狠地摔在地上,在刺耳的破碎声中,我听见自己在说:“既然这些都没有用了,而我们赔的是一副茶具,那这两个东西也要摔烂!”老板立刻跳起来了,整个身子朝我扑来,好在我们人多,老板被我们的人拉住了,后来又骂骂咧咧地离开了。那一天,本来是一场很有情怀的茶叙,我却一直在生气:既然我们要赔整副茶具的钱,那么茶杯和茶托就是我们的资产,自己的资产自己处理,有错吗?老板干吗那么激动?
确实是年少轻狂啊,在千古流芳的斯文圣地,我居然做出了如此有辱斯文的事情,而且当时还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斯文扫地戾气身,只是当时已惘然,杜公,我给您赔罪了啊!
二
在草堂边上上班,我把宿舍也租在草堂边上。记得我的蜗居是在西南财大对面的西窑村二组,一户农民自建房的二楼上,居住条件不大好,一楼是堂屋,房东养了生猪、海狸鼠,很臭,二楼两个房间,我住一间,房东一家住一间。从我的房间窗户望出去,较远处是别的农房,正对着的七八米开外就是一大堆垃圾,晴日群蝇乱舞,雨天污水四溢,空气里弥漫着腌臜恶臭。那是一个垃圾中转点,没有办法改变。在这样的场合生活终究还是令人同情的,但是当时我自己却是不以为然的,一是我作为一个来自大巴山区的小镇青年,能到省会城市找到工作,且有一个小窝,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二是上班近;三是有杜公为邻;再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来不久,我的一些初中高中时的好朋友,就到附近的财大、行政学院来念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