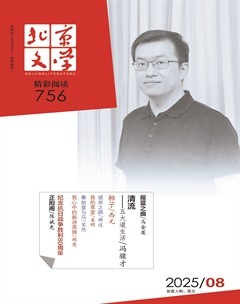一 多多(1951—)
七十年代初期,多多年方弱冠,“是熟睡的夜和醒着的眼睛”,让他得到了神力,居然同时写出了两种作品。一种,比如《致太阳》,“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乃是热血的结果。一种,比如《蜜周》,“我,是不是太粗暴了?/‘再野蛮些/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女人’”,乃是精液的结果。后者成稿于1972年,前者成稿于1973年。前述两种结果呢,也可见于一件作品:比如组诗《万象》,共有十四首,全部成稿于1973年。热血是政治的热血,精液是身体的精液。到了后来,诗人却不再喜欢前者——也许在他看来,那意味着某种余绪、暴力、左派或集体无意识。尽管多多持有此种态度,我们必须要晓得,“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恰好是多多——以及那代诗人——所面临的最初和最深刻的语境。“太阳”“人民”“北方”……多多不断写到这些事物,亦可见出此种语境的力量。但是,我们终究要信任多多的取舍,不仅是因为,《蜜周》早于《致太阳》。在政治抒情诗方面,多多不能,也不愿争锋于江河。他不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小弟,看看吧,他拥有迥异于时人的起点:身体抒情诗,欲望抒情诗,“听凭蜂群般的句子涌来/在我青春的躯体上推敲”。在这些作品里面,词紧跟着句,句紧跟着节,节紧跟着篇,都急着要来见证诗人的青春。那钻石,大颗,小颗,叮当作响,诗人一抓一大把。这是荷尔蒙的夜晚,这是直觉的闪电,这是诗人的泪流满面。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想象力,身体和欲望的想象力,混合着姜夔的感受力;比两者更大更不可抗拒,还混合着茨维塔耶娃(MarinaTsvetaeva)的众所周知的痛苦,以及对于这种痛苦的罕见的承担力。先来读多多的《手艺》:“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再来读茨维塔耶娃的《我的诗……》:“我写青春和死亡的诗,/——没有人读的诗!——/散乱在商店尘埃中的诗/(谁也不来拿走它们)”。两者血缘,一目了然。除了身体抒情诗\欲望抒情诗,还有田野抒情诗。比如,《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当春天的灵车穿过开采硫磺的流放地》,两者都成稿于1983年。虽然多多很敬慕晋人陶渊明,此类作品难臻宁静,相反却将诗人推向了痛苦、狂乱和死亡的预感,推向了陶渊明的反面,或者可以说推向了宋人辛弃疾的正面——诗人也有谈到,他要的就是宋人辛弃疾的“壮怀激烈”。冰雪皇后来了吗?多多大呼小叫:“我要让她好看!”他的力度来自色彩和情怀,来自天马行空的速度感。如果我们首先震惊于某诗人的芒刺,那么稍晚一点儿——必定要稍晚一点儿——就会迷恋上多多的钻石、烈酒、电流和“冷疯狂”。多多是头“大象”,每个瞎了眼的读者,都能够摸到“异象”。臧棣怎么说?“多多是我们诗歌中的达利式的人物,想象力怪诞,然而又能在细节上展示出迷人的精确。”因而正是多多,唯有多多,让臧棣产生了很强的竞技欲望。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多多去了异国,居然也不断有作品问世。来读《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河流倒流,也没有用/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也没有用/鸽群像铁屑散落/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再来读《在英格兰》:“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使我到达我被失去的地点/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耻辱,那是我的地址/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前者成稿于1989年,后者成稿于1990年。两者都有写及故国之思,前者忍受孤独而后者擅长骄傲。当然,骄傲,乃是多多的常态。前文有说到天马行空,实则真有一匹马,一匹天马,奔突于多多的不少于二十件作品。这是一匹嘀咕着的马,一匹吃掉一万盏灯的马,一匹用泥土堵住耳朵的马,一匹脱下马皮的马,一匹被勒紧了的马,一匹被狠踢腹部的马,一匹出棚后被人骑被人打的马,一匹无头之马,一匹从脑子里溢出蝴蝶来的马!这些马都是诗人——也包括时人——的化身,尤以《马》《授》《钟声》《五年》《从马放射着闪电的睫毛后面》和《从锁孔窥看一匹女王节的马》交代得最为明白。诗人就像一匹种马,一匹半自由的马,在跑到山巅之前,“还来得及得一次阑尾炎”。啊,无头之马,无头之马:连柏桦都曾经赞个不休!无头之马,无头之马:终于成为一代人的隐喻!多多终以他的天才,秀出同侪,成为一个罕见的个案,一个两全的个案——他既分担了启蒙的义务,又鹤立鸡群般地完成了艺术的任务。杨小滨怎么说?“多多……以其超越了同世代人的诗性魅力,日渐成为中国当代诗的灵魂人物。”
二 舒婷(1952—)
从某种意义上讲,舒婷是位具有复调(polyphony)特征的诗人。换句话说,她有很多张面孔。1977年5月,诗人写出《这也是一切》,用以赠答某诗人的《一切》。后者冷峻、迷惘、怀疑,弥漫着悲观主义;前者则温婉、坚定、确信,洋溢着少女般的乐观主义。后者是“最后的料峭”,前者是“碧绿的早潮”。那些批评家会说:“喏,两者泾渭分明嘛。”笔者却认为,这两件作品还得往细了说。《一切》乃是今日之诗,绝望之诗;《这也是一切》乃是明日之诗,希望之诗。没有绝望,何谈希望,不堪今日,且看明日。大哥哥有大哥哥的“重轭”,小妹妹有小妹妹的“花冠”,花冠是对重轭的反对呢还是安慰?笔者惊奇地发现,瑞典老汉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居然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舒婷似乎总是在“扮演一位安慰者的角色”。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佐证。就是在此前后,比如1973年,诗人写出《致大海》,1980年,写出《献给我的同代人》,1981年,又写出《会唱歌的鸢尾花》。笔者的斩钉截铁,消除不了他者的小声嘀咕。那就来读《献给我的同代人》,“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再来读《会唱歌的鸢尾花》,“理想使痛苦光辉/这是我嘱托橄榄树/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都是赴死者之诗,都是烈士之遗嘱,有何明日可言?又有何希望可言?诗人当年所面临的危险,今天中学生看来如同“虚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壮烈和崇高,今天中学生读来如同“伪造”。偏见由此而生;甚至有人会认为,诗人给新诗带来的植物,橄榄树也罢,鸢尾花也罢,似乎具有阴性或右派向度上的语义引申。殊不知,这在当时,恰是对革命意象谱系的大胆更新。在笔者看来,这些植物,不是小姐,而是怒睁了双眼的豪杰。“我历来就是撞得粉碎,我所有的诗篇,都是心灵的碎银。”我们已经看到,舒婷与今天派诗人,曾经肩并肩,面对着权力父亲;但是,有时候,她会甩开今天派诗人,转而单独面对权力异性。当她面对权力父亲,是一位斗争的诗人;当她面对权力异性,是一位既斗争又团结的诗人。此之谓复调。1977年,诗人写出《致橡树》,1978年,写出《思念》,1979年,写出《双桅船》,1981年,又写出《神女峰》。诗人设计了理想化的两性关系,“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这种关系和距离有利于两性——尤其是女性——在获得尊严的前提下获得爱情,甚至获得轻度的羞答答的欲望纾解。当其时,这就是抵抗。今天中学生读舒婷,不见抵抗,徒见热烈而已。其实这些作品不像爱情诗,而像单方面的含苞待放的女权主义宣言。从这个意义上引申开,与其说,诗人呈现了爱情的困境;不如说,她呈现了人性的困境。“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今天中学生读舒婷,不见困境,徒见甜点而已。此之谓复调。不管怎么样,此类作品让诗人名声大噪。权力父亲?算了吧,还是瞄准权力异性。当权力异性的压迫——哪怕是从理论上——不复存在,慢慢地,诗人也就只剩下了小布尔乔亚的爱情诗。“我成不了思想家,哪怕我多么愿意,我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大信任思想的加减乘除。”这些爱情诗,富氧,高糖,流通性极高,受到了空前热烈的迎迓。诗人早期的悲剧性,被今天的读者消解;中期的悲剧性,被蜕变的自我消解——她终于成为一位倪萍姐姐般的温暖而团结的诗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今天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通过舒婷,很快就找到了达成和解形成共识的契机。1978年12月,《今天》发表《致橡树》;次年4月,《诗刊》转载这件作品——此后,这件作品就成了保留性的晚会朗诵节目。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诗人已然很少写诗;九十年代以后,重心转向写散文。“文学像一群不善罢甘休的蜜蜂,围困一棵花期已过的老山楂树。”她也曾如此自嘲:诗歌难以破镜重圆,散文也非白头偕老。自1996年至1997年,诗人应邀到柏林生活和写作,居然重启诗笔,写出一批作品,包括长诗《最后的挽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语境,让诗人远离了李清照,远离了普希金,远离了泰戈尔,远离了戴望舒,远离了何其芳,远离了蔡其矫,远离了这些决定性的营养,转而开始尝试新的风格:拼盘,反讽,戏剧性,用口语记录日常。是的,诗人甚至写到了“啤酒瓶”,写到了“葱花鸡蛋汤”。对诗人来说,这已是很大的冒险。诗人也曾反复自问:“也许怀个怪胎回来?”——她尚未悉知,当其时,新诗已经怀上了千百个怪胎。
三 于坚(1954—)
如果说于坚是一个具有较大破坏性的渎神者,可能会得到一些汉学家——比如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首肯;然则文化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渎神者,或正是森林深处的万物有灵主义者。大地、日常、汉语,三者皆有神性。在这个化学和物理学时代,神性如落日,眼看就要敛起最后的余晖。诗人面对一个残存的世界,一个残存的云南高原,一条残存的并未就范的怒江。他总是不断后退,试图恢复这抹余晖的大光明。途穷的生活,天真的写作。先来问,诗人要面对什么样的大地?荒凉、黑暗、潮湿、和谐、羞涩、处女般的大地,万物有灵的大地,只服从于不为人知的律令的大地。高原、河流、怒江、苍山、滇池、无人之野,运气好能够看到成片的棕榈树。在这样的大地上,诗人遭遇了,或者说指望遭遇到大象、豹子和老虎。不是隐喻、象征、修辞的借物,不是纸面上的叶公好龙,而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饥饿而仪态万方的大象、豹子和老虎。诗人乐于与它们对视,并期待着这样的奇迹:双方可以展开一次——哪怕只有一次——咧开嘴的快乐的交谈。同样是在云南高原上,后来,雷平阳也表达过这个意思。1994年,诗人写出《我梦想着看到一只老虎》:“我梦想着看到一头老虎/一头真正的老虎/从一只麋鹿的位置 看它/让我远离文化中心 远离图书馆/越过恒河 进入古代的大地/直到第一个关于老虎的神话之前”。2017年,诗人写出《漫游》:“一片旧高原突然展开 像秋天的机场那样辽阔/蔓草如刺 石砾黯然 似乎刚刚夷为平芜/看不见推土机 尸体般孤独 仿佛这是我/擅自授权的保留地 我自己秘密统治着的荒凉/垂着巨乳的女娲还在补天 我是第一个野兽/唯一的野兽 最后的野兽”。再来问,诗人要面对什么样的日常?琐碎、陈旧、啰唆、不绝如缕、代代相传的日常,身体性和官能化的日常,非英雄(non-hero)的日常,录音带、抓拍或纪录片式的日常。茶馆、电影院、酒肆、水井、菜市场、四合院、乱糟糟的卧室、风花雪月或生意快要做不下去的小作坊。道法自然,大小便无非有机肥。此种日常,低唤大地,而能与大地共生。1984年,诗人写出《尚义街六号》:“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在翻一本黄书/后来他恋爱了/常常双双来临/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昆明话里并无“拭”字,或可改为“揩”字,以帮助诗人避开“普通话”对“方言”的鱼目混珠。最后来问,诗人要面对什么样的汉语?古老、原在、即兴、清洁、地方性的汉语,“为天地立心”的汉语,尚未沦为工具的汉语,只有本义而无引申义和比喻义的汉语。母语、象形、会意、混沌,曾经写出过唐诗和宋词。1990年,诗人写出《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的手再也不能触摸秋天的风景/它爬上另一棵大树 要把另一只乌鸦/从它的黑暗中掏出/乌鸦 在往昔是一种鸟肉 一堆毛和肠子/现在 是叙述的愿望说的冲动/也许 是厄运当头的自我安慰/是对一片不祥阴影的逃脱/这种活计是看不见的 比童年/用最大胆的手 伸进长满尖喙的黑穴 更难/当一只乌鸦 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我要说的 不是它的象征 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 只是一只乌鸦 正像当年/我从未在一个鸦巢中抓出过一只鸽子/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此种汉语低唤日常,低唤大地,而能与日常和大地共生。前文曾有说到,“三者皆有神性”,又该怎样来理解呢?曰真,曰善,曰美,曰信,曰德,曰敬。奈何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城市化和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知识、冒险和物质主义改变了大地,意义、共识、潜规则和高悬之物改变了日常,修辞、拼音、逻辑性和翻译体改变了汉语。因而,诗人的全部写作——诗与随笔——乃是去蔽与招魂的写作,其目的,就是要将大地、日常和汉语重新置于“太初之无”。于坚之诗乃是此地之诗、在场之诗、还乡之诗、去智之诗、先验之诗,乃是肉身之诗、信札与便条之诗,“本然”之诗而非“使然”之诗,“自在”之诗而非“自为”之诗,“此岸”之诗而非“彼岸”之诗,“器”之诗而非“道”之诗,“形而下”之诗而非“形而上”之诗。2010年,诗人写出来读《恒河》:“恒河啊/你的大象回家的脚步声/这样沉重/就像落日走下天空”——雷平阳激赏此诗,“视其为于坚最好的短章”。于坚的大敌是什么?一个是“现在进行时态”,一个是“未来主义”。他没有生活在别处,却通过一意孤行的写作,惊叹和赞美的写作,想要骗过自己,退回古代并混迹于老庄李杜之间。也有骗不过的时候,诗人就会写出哀歌。《0档案》《哀滇池》和《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或可分别视为日常的哀歌、大地的哀歌或汉语的哀歌。诗人尝试着直接排列“名词”和“动词”,辅以“空格”和“长句”,以求得“物品清单”或“冲锋枪扫射”的效果——柯雷把此类“名词”称为“用来命名的词”(words-that-name),又把此类“动词”称为“自己会动的词”(words-that-move)。与其说,于坚已退回某种过去时态,毋宁说,他试图在当代语境里唤醒记忆,唤醒道法自然的伟大文明。于坚所谓汉语,就是白话,他或有不知,与前述文明相表里的非仅白话——因为白话,只是残存的废墟般的汉语。此类矛盾并非罕见,比如,诗人还面临着方言与普通话的矛盾,汉语与英语的矛盾,拒绝隐喻与隐喻的矛盾,古典主义、民族主义与先锋主义的矛盾。矛盾同时带来了挤压力与活力,于坚的写作,乃是一种不可能之可能,所谓个人气象也就在——或只能在——艰难的两难里求得一片昊天。最后,如果要说于坚是一个抒情诗人,请不要诧异,更不要如此反问:一个抒情诗人?一个光头的抒情诗人?一个骑破车的抒情诗人?一个穿着大头皮鞋的抒情诗人?
四 王小妮(1955—)
王小妮仿佛以外省的平民的清癯,响应了北京的沸腾,并让《今天》获得了更加蜿蜒的地理学想象。“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成为北方”。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诗人集团,亦即“朦胧派”,也早已被更加得体地称为“今天派”。某些今天派诗人后来加速遗民化,加速流民化,以托钵僧的艰难和妩媚,化得了“外在”的更为广阔的认同感。王小妮则仍然直面“此在”的生活、命运和危机,并将固执的写作推向了让人惊诧的境界。如果把她强行划入今天派,那么,她既是一个后来者,又是一个立异者,还是一个独在者,以至于她几乎与任何诗人集团都没有关联。诗人从来不欲觅得一位或几位美学同志或美学上级,恰恰相反,她要摆脱他们,就在他们回首并埋首于峥嵘回忆录之际。“磨砺使我走到今天。”诗人也曾谈到她与他们的差异,“使我可以笑着,端着茶杯和它从容对话了。”举重若轻,说得真好。今天派那么冷硬,那么迅疾,那么尖锐,何曾有过从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诗人却以从容而孤独的奔赴,以若干短诗和组诗,挽回了她和他们曾经“共有的光荣”——如果,真有所谓“共有的光荣”。那就重点来谈谈三个组诗,三个死亡组诗——其一,《看望朋友》,共有十三首,写到朋友的死亡,成稿于1992年至1993年。这个朋友见证过苦难和历史,见证过“零下二十度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