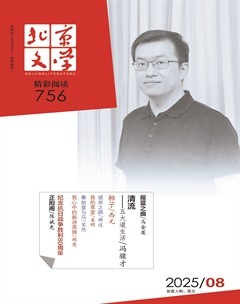《北京文学》推出“00后”诗歌大展,100位“00后”诗人,以集束炸弹的方式轰炸诗歌界。“00后”诗人目前最大年龄不超过25岁。按照艾略特的说法,25岁是诗人的精神转折点,或者说,是诗人从青春写作迈向中年写作、从旧我迈向新我的重要门槛。从这个标准看,“00后”诗人还处于青春写作的时期。这并非贬低或看轻,放眼诗歌史,很多传世之作都是诗人在25岁之前写的,更不用说像济慈、海子这种生命止步于25岁的诗人了。说写诗是年轻人的事业有点绝对,但年轻人的确是诗歌队伍的主力军。他们对世界有尖新的感受力,对诗歌有献祭般的热情,他们的体力、脑力、记忆力、想象力都处于巅峰状态,这些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经验的不足。相比小说家,诗人在年轻时就写出杰作的概率更高。说不定,他们已经写出了诗歌史上的重要作品,只是还没有被辨认或确认出来。因此,对年轻诗人的重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读完第一批的25位“00后”诗人,我的总体感受是:他们普遍学历很高,诗歌风格有明显的学院化倾向,修辞繁复,意象密集,以巴洛克式的语言装饰生活的细枝末节,在有限的经验之内拓展想象的国度;他们注重意识的流动,善于抓住微妙的情感瞬间,让心象与物象彼此映照,形成和谐统一;他们喜欢把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专业领域的术语,嵌入日常生活的表达,以达到某种精确感或陌生感;他们除了聚焦个人经历,也有现实、历史、地理等题材的书写,但他们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即使触及比较厚重的话题,也会纳入个体感受的轨道上,试图建立起自己和时代之间的脉搏感应;他们偏爱叙事胜过抒情,偏爱浅唱低吟胜过引吭高歌,如果八十年代诗歌是广场喇叭,九十年代调低成室内乐,新千年调低成家庭音响,现在则进一步调低成耳机里的嗡鸣,它可能只适合读给一个人听,这个人还可能就是诗人自己。
当然,以上感受不能作为“00后”诗人整体特征的概括,只能算是我看到的部分“00后”诗人的轮廓勾勒。任何时候,我们应该警惕整体论,尤其是将它运用到一个最强调个性的诗歌领域。正如电影《放大》所揭示的,对于同一事物,远观和近看,完全是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