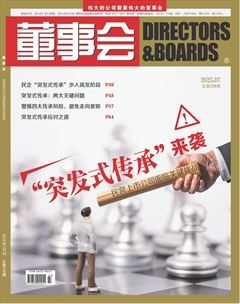继承之战:财产纠纷是否会引发控制权之争?
最近,浙江某集团公司董事长长女在杭州与香港两地被其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妹起诉。
在杭州,三名原告要求获得其父(被继承人)生前承诺的各价值7亿美元的信托基金权益,申请法院调取其父的血液样本进行DNA比对,并要求分割其父(现由长女)持有的集团公司29.4%股权。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判决确认三名原告享有收益权,下令被告不得从相关账户中提款或转账任何资产,禁制令持续有效至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最终裁决为止。同时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擅自转移的信托财产损失等。
微评
上述案件的核心是继承纠纷和家族信托资金纠纷,目前并未发生所谓“境内的股权争议”纠纷。不过,无论杭州与香港两地诉讼结果如何,都将对相关集团公司的股权架构、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目前,该集团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持股46%的地方国资,董事长长女持有29.4%的股权,其余24.6%的股权由职工持股会持有。若杭州法院支持三名原告的继承权诉求,则董事长长女继承自其父的29.4%的公司股权,将被重新分配,其持股比例可能会降至10%以下。这会对集团公司控制权、公司治理架构、未来各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分配以及他们各自对整个集团公司、关联公司以及对外投资活动产生结构性影响。不过,这些影响也只局限于29.4%的股权范围之内,对集团公司整体治理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相反会削弱每一名继承人作为股东对集团公司的影响力。
相比而言,香港的法院判决对集团公司治理的影响更为复杂,也更难以推测。原因在于:
第一,2003年被继承人设立离岸家族信托时,由于当时资金不足,信托仅注入部分启动资金,剩余款项需通过公司分红逐步补足。上述情况是否真实准确?尤其是相关信托合同和信托文件对持续补足资金的具体约定是什么?需法院审理后方能确定。
第二,2024年2月被继承人去世后,对信托的继续注资已经停止。这一事实对信托关系的影响是什么?须依据香港法律判定。
第三,2024年5月从信托账户转出110万美元,到底是“恶意侵占遗产”,还是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的合法操作?均有待法院审理明断。
为避免干扰杭州法院对案件的审理,香港法院宣布,相关禁制令持续有效至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有最终裁决为止。这可能是香港法院在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裁判空间和余地吧。
另据《2024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我国仅有38%的家族企业制订了正式的继承计划,但涉及非婚生子女权益的安排近乎空白。继承安排的缺失,显然不利于家族企业稳定预期、行稳致远。
家族信托被“击穿”,争议何在?
近日,根据案号为(2023)苏0602执6286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法院将被执行人崔亦某名下的4143万元“家族信托资产”当作存款予以强制执行。由此引发争议:法院可否将信托资产直接认定为“存款”?这一做法是否突破了信托法所确立的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如果法院要对此“存款”予以扣划,在程序上有何具体规则与要求?
微评
该案具有典型意义,不仅触及现代信托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也触及信托制度与程序法的衔接问题。简单来说,既有信托实体法问题,也有民商事执行程序问题。
从实体法角度来看,第一,信托法上对“信托财产”有明确定义,执行裁定书中关于“信托资产”的表述,并不严谨、准确;在逻辑上,“信托资产”的范围远大于“信托财产”的范围,信托关系当事人所能委托、处分、管理以及取得收益的信托财产与信托资产,虽相互有关联,但在具体内容与细节上各不相同;同样,对诉讼与仲裁的裁判者而言,是否可以不问“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的差异而概括裁断,的确需要慎之又慎。第二,即便将执行裁定书中的“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不加区分、仅仅当作同义词来看,也存在法院可否将其直接认定为“存款”的问题。在金融法上,“存款”是一种以资金借贷为基础的特定金融产品。它具有明确的、特定的含义,特指资金所有者与商业银行通过订立储蓄合同或存款合同而存放于商业银行的货币资金,依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的基本储蓄存款原则。判断、认定一种金融产品的属性与类型,在金融产品发行销售之初,便已经由金融监管机构通过金融业务许可制度进行了界定。如果法院可以通过执行裁定书来改变金融监管机构事先对某一金融产品属性的界定,似乎会架空监管。第三,通过执行裁定书将家族信托财产直接认定为“存款”,可能突破了信托法所确立的信托财产独立原则,损及信托关系的稳定。
从程序法角度而言,第一,在实体审理中,即在该案生效判决书中,并未对案涉信托财产是否为“存款”做出裁决。第二,执行程序中,法院可否通过执行裁定书来补充、追加判决书中未处理的诉讼请求或事项?这不仅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也涉及他们在程序法上的诉权,包括上诉的权利。第三,执行裁定书能否对涉案信托财产的性质等实体性问题直接做出认定?抑或执行裁定书仅可以对执行中的程序性问题做出裁定?
通常,若当事人对执行环节存疑,或许应告知执行申请人,并由其向法院提出设立该家族信托的财产不具备信托上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例如信托财产的来源属于违法所得,或涉嫌逃避债务,启动认定信托无效、撤销信托的确认之诉,而非由执行裁定书来认定财产属性,直接扣划,这或许更具说服力。
简单总结一句:家族信托财产或许可依法“击穿”,但公法程序万万不得被“击穿”。
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董事会“说不”
6月30日,ST新潮(600777.SH)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称,会议审议的《关于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0票,反对7票,弃权0票”。此前的6月19日,ST新潮董事会收到由合计持股10%以上的6名股东组成的提请召集人提交的函。提请召集人共同联合提请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函中所附由4名股东提出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新一届董事、非职工监事等3项提案。
微评
ST新潮现任董事会反对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理由引人关注。其关键的反对理由是:鉴于提请召集人虽提出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的请求、但并未以其名义提出具体提案,而与此同时提案人提出的相关提案并不构成有效提案、依法不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故董事会依法拒绝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对于第一句,显然,召开股东会、临时股东会等会议时须准备具体的审议事项和提案,此乃会议召开的必要事项和条件之一。新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第五十八条对此都作出明确规定。
董事会要求提请召集人提交临时股东会将要审议的具体审议事项和提案并不过分,但是否应“以其名义”提出具体议案并非新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的原文表述。
后半段“提案人提出的相关提案并不构成有效提案、依法不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是非常重要的反驳。
对于股东临时提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为防止股东临时提案权的滥用、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设置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提案股东应当满足规定的持股比例要求,且需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书面提交”临时提案(换言之,其前提应为股东(大)会通知已发出)。因此,在公司尚未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情形下,4名股东向提请召集人及董事会提出临时提案,不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相关提案不构成有效提案,依法不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尚未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为由,认为相关提案不构成有效提案是否有理?这或可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第一,从程序合规性角度考察,即该提案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程序性要求?第二,从实质合理性角度评估,即该提案是否体现公司整体股东利益,是否对特定股东的合法权利构成不当限制?总体而言,应坚持“实质优于程序”的基本立场,即在不影响股东大会正常召开和公平表达意见的前提下,程序瑕疵原则上可以通过补正予以弥补,不宜据此否定提案的有效性甚至进而剥夺股东的基本权利。
此外,董事会对拟提交股东会、临时股东会审议的提案或者审议事项是否有审核权?新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后半段规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外。”这里“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是一个非常宽泛模糊的地带,很难加以明确定位、定性,实践中常常被董事会拿来对抗股东的临时提案。
此前,伊泰B股对ST新潮发起收购。如果提请召集人背后所代表的是持有公司50%以上股权的大股东,那么ST新潮董事会再怎么全票否决召开临时股东会,也无法撼动公司股权结构变动的力量吧。唯一的变数就是:拖到退市,让你收购个“寂寞”。
点评人杨为乔系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