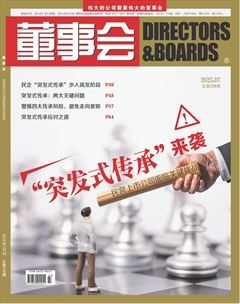董责险作为舶来品,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尤其在信息披露领域,由于缺乏系统性规范,实践中信息碎片化、披露标准模糊、披露形式僵化等问题频发,影响投资者准确评估与市场价格判断。为解决这一问题,需立足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构建契合本土化的董责险信息披露机制
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证券法大幅提升公司董监高的履职责任,加之“瑞幸咖啡”“康美药业”案等司法案例的推动,作为董事免责机制的董责险,一改此前不温不火的局面,在上市公司中迎来投保热潮。而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董责险制度,进一步推动董责险市场驶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4年年底,A股市场共有1205家上市公司公开披露董责险投保计划,董责险从相对小众的保险产品发展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我国董责险制度不断深化发展与广泛应用中,其制度缺陷逐渐显露,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成为阻碍其发展的显著因素。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董责险信息披露制度,只有部分上市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披露其拟购买董责险的意向,且披露的信息有限,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公告只披露拟购买董责险的保单最低责任限额和保险费上限。至于公告后上市公司是否实际购买、保单到期后是否续保、保单实际责任限额与保险费是多少等董责险信息,均未向社会公众披露。
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影响投资者决策和市场效率,尤其董责险主要依据投保公司的经营计划、治理状况等评估其风险情况,相关信息对投资者决策及市场价格波动至关重要。因此,规范公司董责险信息披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利益平衡为视角,建议采取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区分不同市场主体特征,制定差异化披露要求和披露标准,从而建构符合我国市场特点的董责险信息披露机制。
平衡多元利益:董责险信披具有正当性
投资者权益与公司利益的平衡
为公司设定信息披露义务,并非以投资者利益绝对优先而牺牲公司权益,信息披露与商业秘密保护表面对立,但实质统一。信息披露的节点决定信息的价值,不同时间披露的信息会在市场中引发不同反应,因此适度的保密能够防止信息提前泄露导致的市场反应钝化。而从信息披露内容角度讲,对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的敏感信息进行审慎披露,恰恰符合证券监管的重大性标准,是维护市场秩序的理性选择。因此,董责险信息披露与公司信息保护并非根本对立,而是通过制度协同实现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双重保障,董责险信息披露机制的构建大有裨益。
然而,由于我国市场存在若干交易成本,公司信息披露的主动性将受到限制。自愿性信息披露往往面临信息传递不畅的难题,导致信息不对称的不利效果,同时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公司公开披露后可能被竞争者利用,被迫成为搭便车现象的受害者。另外,信息披露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对价格与价值的对应关系造成了干扰。特别是在我国,证券欺诈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加剧了道德风险的产生,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造成负面影响。披露方通过隐藏对自身不利的信息以及夸大有利信息,以实现对证券实际价值之上超额收益的获取,造成价格信息的噪声化,从而削弱了信息作为市场信号的传递能力。因此我国董责险信息的自愿披露缺乏市场支持,有必要通过公权力介入加以规制,以维护投资者知情权。
董事履职保障与公权监管效能的平衡
商事案件的高效处理与市场主体权益的保护平衡,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关键命题。董责险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需审慎平衡公权力监管效能与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之间的张力,既要通过充分披露确保监管效能,又要防范过度披露损害公司利益。
作为连接董事责任风险与市场治理的关键节点,董责险信息披露成为监管机构识别系统性风险的依据,当董责险出现异常承保条款或费率显著高于行业均值时,披露信息有助于监管部门尽早启动核查,迅速处置财务造假、信披违规等风险,实现精准、高效监管。但是,作为以董事为主要主体的责任保险,在对外信息披露促进执法效率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董事作为公司决策的核心主体,过度披露可能导致其面临不当诉讼风险。实证研究表明,当董责险条款被过度披露时,原告往往会针对保险限额提起更高额的赔偿请求,产生“深口袋效应”。二是董责险通常包含董事的个人责任条款,若不加区分地披露可能侵犯董事隐私权,且过度的信息披露要求可能导致保险公司提高保费或退出市场,最终损害董事获取合理保障的渠道。因此,公权力介入董责险信息披露虽具有正当性基础,但应当把握合理限度,避免不必要的信息泄露。平衡公权力介入的执法效率与董事利益保护,本质上是对市场秩序与公司自治的再平衡,由此既能压缩监管时滞、提升违法成本,又能守住公司核心利益的保护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