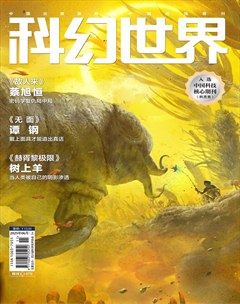“手臂打开。”身着制服的女士敲了敲舱壁,对我说道。
我听话地张开双臂,按照要求在头顶上围成一个圆,看着仪器的合金臂像在医院做透视一样,从上到下缓缓扫过我的全身。
走下检查舱后,她又指示我站在一个小台子上,两手从我的头发一直拍打到脚尖,再次细致地检查了一遍。
即便技术已经连衣服上线头都能识别出来了,也要人亲自来一遍。这遍检查后,她终于点了点头,后退一步放行。
我从另一位工作人员那里接过手机——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其他物品和包一起存在前面——这才终于转过身,整理了下外套,向等在一边的男人走去。
“没经历过这么严格的安检吧?”他笑着说,试图让我放松。
我勉强扯了下嘴角,“嗯,第一次。”
“不用害怕。”他说。男人姓张,是名律师,个子虽不算矮,但人很精瘦,显得身板仿佛也小了一圈。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他的西装垫肩松垮地垂下来,像高中生偷穿了大人衣服。
“她其实没什么攻击性,挺好相处。”张律师说,“而且警卫就在门外,万一闹出什么乱子,他们第一时间就会进来保护你。”
我点点头。我的确忐忑,但不是因为这个。
“伦理委员会那边怎么说?”明明是重要的问题,他却故意用闲聊的语气问出来,反而刻意得难受。
“说……”我重复早上刚听到的话,“还是得和她见面聊聊,确认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们才好开展责任鉴定。”
“嗨,我就知道,这种事,都是推来推去。”他一副老成的语气说,“没人愿意给这种案件担责……我们到了。”
我抬起头,看到面前的黑色金属大门上一行铅白色的字:蓉城看守所3号会面室。
张律师在我身前,抬手敲了敲门。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家里正一片忙乱。
“我只说再睡十分钟,谁知道再一睁眼就这个点了……”许晓宁一边忙不迭地把裤子往身上套,一边解释道。我来不及和他说什么,跳下床,穿着睡衣就快步向儿童房走去。
我对天发誓,开门的一瞬间,我瞥到许叶洲猛地一个鲤鱼打挺钻进被窝,蒙住脑袋装睡。
小兔崽子,果然早醒了。
“小洲,起了!”我装作无事发生地开口,放她一马,“你爸睡过了,收拾下就去学校,早饭路上买。”
“嗯……”她装模作样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揉眼睛伸懒腰,做戏还挺全。我笑着看了她一会儿,正打算调侃两句,家里的电话十分突兀地响了起来。
如今智能家居的蓝牙已经接通了手机信号,这个铃声是我的,可是号码我不认识。
“接通。”我说,“您好,哪位?”
“是陈曦博士吗?”电话那端,一个男士公事公办地问道,“我们这边是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需要找陈博士沟通一下‘视界’眼镜的相关问题。”
话音一落,家里仿佛被按了暂停键。女儿毛衣套到一半便停下,刚从卧室走出来的许晓宁也在走向厨房的路上停住了脚步。
我停顿了一秒:“……是我,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男士解释道,“三天前,蓉城发生了一桩命案……”
“您等一下,我在外放,有未成年人在旁边。”我忙说,不顾女儿好奇的眼神,匆匆转身去了客厅,接通自己的耳机,“不好意思,请说。”
许晓宁很有眼色地恢复了动作,去找女儿,我则站在客厅的角落专注聆听。
“打扰您了。”男士客套道,“犯罪嫌疑人是一位女性,四十五岁……”
只比我大几岁,我心想。
“……她是一位视力障碍者,”他说,“犯案的时候正戴着‘视界’眼镜,版本是v12.5。因此,我相信您也明白,按照惯例,是需要对您主导研发的这款眼镜进行测试分析,来进行责任鉴定的。如果是眼镜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她看到了什么幻觉……”
“视觉偏差。”我说。
“不好意思?”
“请尽量避免使用‘幻觉’这种定义模糊的词,是视觉偏差。”我说,惊讶于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不专业,“我在研讨会上多次强调过这一点。”
“……好的。”对方迟疑地说道,“总而言之,分析需要您的协作。毕竟据我了解,目前的‘视界’眼镜还无法回溯,看到她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场景……”
“个体视力基础不同,加上私人设置参数,为了保证高时效性,没有足够内存保留……算了,”我叹了口气,看来委员会青黄不接也是常态,“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
“这个,明天上午可否请您来委员会沟通一下,确认眼镜性能?”他说,“没问题的话,下午也请您在对方律师的陪伴下,和犯罪嫌疑人见一面,确认她当时的那个……参数,弄明白她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异常场景才杀人的。”
“可以。”我说。
确认了时间地点后,对方说了再见,我才突然想起来,“等一下,”我叫住他,“我能不能问问……案件情况?”
“哦,您看一下新闻就知道了。”他说,“她谋杀了她的丈夫。”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留我一个人愣愣地站着,视线落在门口,许晓宁正一手拿着小洲的书包,蹲在地上帮女儿换上她的小球鞋。
“视界”眼镜v1.0的发明,还早在2020年。
机器视觉技术在那时就已经成形,且颇具规模。当时是谷歌眼镜主导,与机器视觉研发公司合作,制作了一款可以协助盲人和视弱者的眼镜——说来简单,只是给眼镜匹配了一个摄像头,将看到的画面通过机器视觉算法分析进行识别,再通过耳麦向盲人描述具体的内容。
听起来神奇,但当时的技术缺陷也很多。例如,虽然能进行物品识别,但对距离的判定因为受到身高和动作的影响,还是很难精准;而光照的不均匀、镜头对场景的畸变,甚至像素的高低,都会导致识别出现问题。更别提生活中的物品本来就不是统一模型的样子,木桌是桌子,罩着桌布的木桌是不是桌子?三只脚的呢?被砍掉一半变成斜面的呢?
对人类来说,这些问题很好判定,但对机器视觉而言,每一个都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专门解决。
因此在当时,“视界”眼镜虽然噱头很足,但实际上对盲人来说还是很鸡肋。盲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熟悉的环境里对周围的物品都有感知,不需要眼镜;而到了陌生环境后,眼镜单纯指出前方有什么,又没法解决他们最需要的距离和细节的问题。
“视界”眼镜真正得到推广和运用,是迭代到v8.0版本以后,这还是几年前的事。
人的视觉原理说来也不复杂。眼睛对外界事物感光,画面通过小孔成像,倒映在视网膜上,随后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将画面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中的神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加工分析,完成识别等一系列工作。视力障碍者出问题的地方也就在这几处,晶状体灰化导致无法感光,视网膜病变脱落,或者眼部压力导致神经受损无法传递信号,等等。在当代医疗中,视网膜修复手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因而其他90%以上的视力障碍都出在最初的感光和神经的传递上。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两个问题可以用同一个方式解决——用摄像头“看”事物,对它们进行机器视觉识别,并将相应的信号直接传递给神经系统。
这样一来,机器做的事情也相对更加明确——看到画面、重构画面,根据画面进行信息的提取和识别、形成信号,而将信号传递给大脑后,剩下的过程就由人类原有的神经系统接手了。
换句话说,这种方式不再是以前那种让盲人“听到”眼前是什么,而是真正“看到”。
真正意义上的视力恢复。
2020年尚达不到的技术,如今可以做到了。“视界”眼镜v8.0刚一上市,就收获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哪怕当时的版本还有很多问题,如画面经常变形、识别经常出错,也拦不住购买的热潮。毕竟看到光明,是每一个盲人都渴望的事,哪怕看到的是完全不真实的事物。
从那之后,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画面识别越来越清晰正确。到了现在,最新的版本v12.5——正是看守所里那位女性使用的版本——已经几乎和普通人的眼睛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边缘场景、识别误差,我们管这些问题叫视觉偏差。
和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这项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眼见不一定为实,你以为你见到的,和你真实见到的东西是不同的。’”会议室内,一位女性委员指着“视界”眼镜说明书逐字念道,“陈博士,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软木椅子上不舒服地动了动。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的伦理委员会,已经没有人会去参加研讨会了吗?
“这个……”我决定从头说起,“我国有个很古老的故事,叫‘两小儿辩日’,您听说过吗?”
面前的几位委员都点了点头。
“一个小孩称,太阳中午小、早晚大,说明中午远、早晚近;另一个小孩说,太阳中午热、早晚冷,说明中午近、早晚远。”我快速总结道,“现在我们都知道,真实情况其实是第二个小孩正确,相对而言,太阳在中午略近一些,早晚远一些,而且人其实无法识别其中的微小区别,应该是差不多大的。可是新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早晚见到的太阳,比中午时候的大呢?明明距离更远。”
“中午光线强,影响视觉?”一位男性委员问,我摇了摇头。
“这么说的话,月亮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月光的强度并不足以影响视觉。”我说,“这事实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视觉与认知之间有偏差的例子。人类是为了能在地球上生存而进化至此的,因此人类的眼睛,也停留在一个对‘地表附近’的事物认知更为精确的水平。我们看头顶的太阳时,要么没有对比,要么对比只有云彩,而看地平面附近的太阳时,对比对象是遥远的地平线和远处的建筑物,所以在我们脑子里,地平面有一个‘很远’的概念,而对天空和云则没什么实质性的概念。因此,即便中午和早晚的太阳在视网膜上都形成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投影,我们的大脑也会自动认为地平面‘很远’,在那里的太阳也随之‘很远’,而它仍然这么大,所以应该相对较大——这是人脑自动完成的透视补偿。作为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太阳,这也叫作庞佐错觉1。”
“……也就是说,”消化了一会儿,坐在中间的那位女士推了下眼镜,“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差不多大的太阳,但我们的脑子认为早晚的太阳更大,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早晚的太阳更大?”
我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所谓视觉,其实不是光学,而是一种认知。”
几位委员相互看了看,一位男士在那个女性委员的耳边说了两句。
“这和‘视界’眼镜有什么关系呢?”她问道,“是不是说,机器看到的事物,和实际传递出去的信号有可能不一样?”
她很聪明。我说:“连人类大脑都会出错,机器的问题就更多了。人脑毕竟是一个从小被各种数据训练了几十年的精密仪器,而机器视觉高度依赖于算力和数据,可能出现的问题更多更繁杂,这也是‘视界’眼镜研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都出现过哪些情况呢?”她问道,“可能会有哪些……视觉错觉,极大地影响人的认知,导致她精神错乱,对现实误判,不小心致人死亡吗?”
我张了张嘴,一时沉默了。
她问到了关键。
走进会面室前,我想象了很多黄女士可能的样子。
新闻里说得简略,只说一位黄姓女子在室内杀害其丈夫李某,随后一直留在案发现场,直至被邻居发现并报警。没有附照片,杀害的方式据说是她把李某从他们那个公寓的二楼推了下来。警方经过勘察,排除了李某意外跌落的情况,确认是黄女士推的,现在问题只在于她是蓄意谋杀,还是意外致人死亡。
之前约见面的时候,张律师给我补了课。李某是位银行职员,黄女士在附近中学当老师,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不算富裕但经济也不紧张,两人住在蓉城一间精装公寓内,是一对非常普通的夫妇。据说,夫妇两人一直相处和谐,档案清白,都没有犯罪记录,邻居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矛盾或是家暴之类的情况。
“她说什么了吗?”我问张律师,他摇了摇头。
“拒不配合。”他说,“不肯说事情经过,也不肯说自己看到了什么。事实上,从被捕到现在,她什么都没说。一般这种就按事实确凿无异议判了,但她这例子又特殊……你懂吧,那个身心障碍人士保护条约……”
我点点头。一方面是当代法律对失能、残障人士的保护,另一方面,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任何涉及新技术使用的社会事件,恐怕都要经历这么严格的责任划分,让伦理委员会对技术的发展起到监管职责——至少他们是这么宣称的。
“所以还是得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确认权责范围,这样我也有材料给法官看,尽量给她争取一个合理的判罚。”说得跟真的一样,我心想。事实上这种案子是当代热门,有助于提升律师的声誉。
进门之前,我脑子里最后想象的是一位表情严肃、行事刻板、穿戴一丝不苟的高中班主任形象。所以当真正看到她的时候,我稍微吃了一惊。
她……并不胖,但有一张圆脸,手臂也圆圆的,个子不高,头发在肩上打成卷,给人一种很和蔼可亲的印象,连脸上细微的皱纹都长得很让人舒适。警卫为我们开门的时候,她在椅子上向后缩了缩,低着头,神情却并不像畏缩,反而显得很安静。
是会在邻居家看到的那种很爱种花的阿姨,喜欢笑眯眯地坐在院子里,邀请你去她家喝杯茶的样子。你在她身边坐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世界的节奏都慢下来了一样,安心又自在。她是这种会给人很舒适的感觉的中年女性。
这样一位女性……谋杀了她的丈夫?
再怎么说,和我想象的还是大相径庭。我犹豫着看了眼张律师,几乎要等他开口说“找错人了”,然而并没有。他只是对警卫点了点头,把对方让出去,然后拖开桌前的两把椅子,示意我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