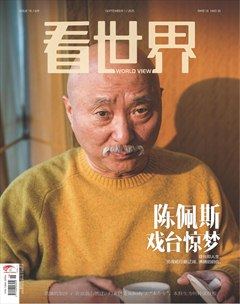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现在热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真诚而完整地回顾了这段沉痛的历史。
很多人会将《南京照相馆》与16年前的《南京!南京!》对比。《南京照相馆》没有聚焦铁与血的宏大场面,创作者在情感上的细腻和生动,让这部电影自点映开始就收获好评不断。
在战争发生前,照相是普通人的生活,是饱含温情和永恒的动作。但在那段黑暗的时空内,一切都被颠覆了。《南京照相馆》将“铭记”这两个字寄予在“照相”之上,因为罪证的留存与铭记同样重要。
从隐性到显性
英文中, “开枪”和“拍照”都是“shot”,动词为“shoot”,一种瞬间性的迫击动作。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子弹出膛的一瞬间,两个动作对照剪辑的画面和意象,贯穿《南京照相馆》。
一个是死的象征,一个是永生的象征。子弹射出,日军的摄影师按下快门,将这一残忍瞬间亲自定格,罪行被当作功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闯入南京的时候,城内还约有10万名国军士兵。但日军进城后,当天就屠戮了大量中国军人。时任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唐生智虽然口头表态要与南京人民生死与共,但在形势失控之前,他却选择携家潜逃。
群龙无首,血染南京城时,军与民都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日军对着安全区医院扫射,凡身上有伤的,无论军民一律射杀。走在城头街上,凡腿上绑带的、肩上和手上有老茧的,同样不问分毫直接击杀。
因为身着的邮差制服与军人太过相似,刘昊然饰演的青年苏柳昌(阿昌)也不得不脱帽除衣。这一设定也暗示着,全片并不会将镜头对准兵与兵的对决,不会大面积刻画过往历史片里的战争场面。
对大多数人而言,刀枪与血腥的闯入,首先带来了生存层面的冲击。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本能,都是求生与保命。只不过,一些人选择隐忍和躲藏,就像照相馆的老金一家。另一些人选择投靠日军,认为今后会是日本人的天下,此刻投敌,是为了活下去,就像汉奸王广海。
邮差阿昌原本也想逃命,他错过了离城的车,慌不择路,跌跌撞撞,遇到日本人,也不是攻击,而是躲藏,甚至是求饶。在那种群体性的绝望和恐慌之中,也有军兵想伪装成平民,也有人想做逃兵,这些都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电影没有回避这些人。
但随着战争继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战场里染上鲜血,也都在各自所目睹的、“shot”的那一瞬间,进入了战争。一个真正进入战争的中国人,是不可能不恨、不悲、不勇的。
导演让观众看到了这些复杂的情感从不明显到明显的过程。片中有几个情绪烈度明显的镜头,分别对应着几个人物内心的转向,微小,但有力。
阿昌第一次潜入照相馆后,本想逃出去以免被连累。他小心翼翼地摸索到路口,发现日本人正在巡街。阿昌亲眼看见他们点火烧死了藏在街边店铺里的中国人、嘻嘻哈哈地用屠刀枪尖对准国人,悲愤的眼泪涌入他的眼眶,但他只能强忍,不敢发声。
被戏女偷偷救下并藏在行李箱里的逃兵宋存义,原是被强行征兵的警察,与弟弟失散后,本来也抱着苟且的心态,想要寻求一处藏身之地偷生。这号人物对战争的感知原本是懵懂的,他们身上的“小我”是大于“大我”的。
然而,在影印房里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日本人送来的照片,看见包括自己弟弟在内的无数中国人被日本人残忍虐杀时,宋存义内心深处的大我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