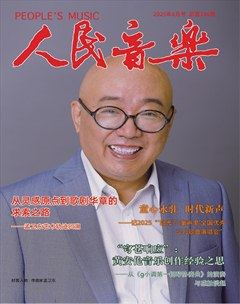缘起
2024年10月11日,我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为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携手厦门爱乐乐团奏响黄安伦的《g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以下简称《g小调》)。时光回到十三年前一一2011年4月16日,我刚回国任教,作为该作品的华人首演者,在厦门艺术剧院与黄安伦指挥的厦门乐团合作。2012年4月21日,我与徐东晓指挥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在北京音乐厅再次演奏该作品,此后十多年里,我数次演奏了黄安伦的作品,并与其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以演奏者的身份也参与了他的“创作”,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演绎经历着一个类似“得其曲、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人"的过程。
黄安伦成长于现代音乐蔚然成风的20世纪,创作理念却更多受到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影响。他多次跟我提到一个词汇一“穹苍响应”,并说这个词汇形象地体现了他对音乐与音乐美的理解。他强调“艺术家的最终任务不在于表现自己”,“‘穹苍'是一切艺术灵感之源头,人人都可得到这份灵感,努力求索的程度会决定‘响应’的程度”。他认为,“‘美就在你的心里'实际上是一种桎措,把人拘措在自己的意念里,而听不到浩瀚深邃宇宙传来的穹苍之音”①。在我看来,这些表述既含有音乐家生命里的神秘经验,亦可追索其现实根源。黄安伦的“穹苍”不仅是宇宙的穹苍、精神的穹苍,更是生命的穹苍、文化的穹苍。
作曲家的“响应”也因“穹苍”的丰富性具有了多维的构成。它至少包含着四个维度:1.民族情结与人类情怀的响应;2.东方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响应;3.传统音乐思维与现代作曲技法的响应;4.虔诚人生信仰与现实人文关怀的响应。它们贯穿于作曲家创作的每一个阶段,成为其音乐作品最具有标识性的美学风格。
得其曲:一代人的心灵史
《g小调》完成于1982年11月,创作要追溯到1976年,结束了塞北军垦生涯回到北京的黄安伦,站在那个悲壮的广场,来自中国塞北大地的深沉旋律,与少年时代聆听巴赫那些仿佛来自天国的神圣之音,构成了跨越东西慰藉灵魂的回响。面对一代政治伟人的人生谢幕,他从时代的悲伤与狂热中感受到人性的脆弱与坚强、高尚与卑劣。他将心底涌起的一段旋律匆匆记录在手掌里,这段旋律后来成为《交响音乐会第一号》(以下简称《交一》)和《g小调》的主导动机。1984年,黄安伦带着他的《交一》归来,这是一部包含《c小调交响序曲》《g小调钢琴协奏曲》《C大调交响乐》三首乐曲的系列交响巨构,同年8月由李德伦、郑小瑛联袂指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完成了首演。苍凉的塞北之音与西方古典形式的神圣气质发生了奇妙的化合作用,其思想内涵整体呈现出作者在70年代自我成长与蜕变的心路历程,构成了那一代共和国同龄人心灵史的音乐书写,也是黄安伦民族情结与人类情怀的第一次响应。
《g小调》是大型交响音乐套曲《交一》中的第二部分,也是一首可以单独演奏的钢琴协奏曲,由作曲家题献给挚友美国钢琴家班诺维兹(JBanowetz),并由后者在1983年首演于广州。②这是一部情感丰沛和民族气质鲜明的作品,也是需要极高演奏技巧才能驾驭的织体复杂、层次多维的钢琴作品,以至于班诺维兹调侃作曲家:“你怎么写得这么难,我得要用三只手才能弹下来。”③
随着《g小调》的公演和 CD 的发行,这部作品在欧洲严肃音乐领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美国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VanCliburnInternationalPianoCompetition)主席乔达诺(JohnGiordano)评论该作品:“不仅作者的成熟技巧与巨大才能跃然纸上,吾人更从中看到了中国的伟大。"①英国伦敦爱乐乐团董事马尔克斯博士(Dr.C.Marks)写信给班诺维兹:“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你首演的黄安伦《g小调》,非常惊讶!20世纪竟然还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仍然不为人所知!谢谢你这精彩绝伦的演奏,我要立即把它纳入我们的曲目,介绍到欧州来!”该作品的上演同样在国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作曲家季西安为此两次撰文,毫不掩饰对它的偏爱,认为从中看到了中国文艺复苏的希望,回答了世界的挑战。在《永恒的颂歌》一文中,他提到:“在《g小调》中,作曲家以娴熟的技巧和火一般的激情,表现了光明战胜邪恶、美战胜丑的搏斗精神,并以他内心博大的胸怀以及独特的审美视角,讴歌了对故土、对民族、对人类的永恒的爱。"⑥
2010年,我刚受聘于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通过作曲家鲍元恺先生的引荐从黄先生那里得到了录音和谱子。刚拿到乐谱时,我震撼且惊讶,钻研这部与自己同龄的作品并没有感到代沟,反而与乐曲释放的强大情感张力产生了深切共鸣。这是一首很特别的作品,大概因为塞北民歌主题音调与五声性调式的缘故,在它气势恢弘的风格背后,更具有东方的凝重、诗性与禅意,内敛而含蓄。那些连绵的长句、奔涌的旋律,恰如这部协奏曲后来被赋予的标题“巨龙"那样,豌蜒盘旋于华夏大地,那是长城、黄河、长江这些中华民族精神意象的声音转化。那些因为现代技法所导致的冲突与张力,仿佛是对这个历经苦难的伟大民族的历史书写,悲壮而崇高,这种粗、激越的美感,激发出我沉积多年的怀乡之情,在跨越年龄、时空的共鸣中,我深切地理解了那一代中国作曲家所经历的跌宕人生,以及他们深沉的民族情感和追求永恒艺术信仰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