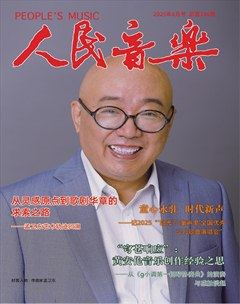24年12月4日至6日,“李西安先生纪念活20 动”在李先生的家乡哈尔滨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音乐学院、《人民音乐》编辑部、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及哈尔滨音乐学院联合主办,是自2020年季西安先生逝世以来首次举行的公开纪念活动。三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李先生的生前友人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季先生的艺术成就,探讨其音乐学术思想对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深远影响与启示。
李西安先生(1937一2020)是我国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传统音乐分析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对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曾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音乐》主编等重要职务。在20世纪末中国音乐面临转折与变革的关键时期,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并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中国音乐在新时代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值季西安先生五周年忌辰之际,本文通过梳理其生平轨迹,结合其理论建树与实践探索,系统阐释先生的音乐学术思想,以期为当代及未来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空间”:李西安音乐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基石
20世纪80年代,李西安先后发表了《中国音乐的大趋势》《走出大峡谷》和《中国音乐的新浪潮》等探讨中国音乐发展趋势的文章。当我们于四十年后重新回顾时,不禁心生疑问:是何种动因促使他提出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构想,并在最大程度上与当代音乐的发展趋势相契合?从其过往经历来看,一方面,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所阐述的信息革命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为季先生带来了现代观念的启示;另一方面,自幼浸润于民族音乐文化土壤的经历,则为他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根基,
(一)成长经历中的民族音乐基因形塑与思想浸染
李西安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市,之后与家人先后定居哈尔滨和天津。他从小学习二胡,并在高中时期师从俄侨音乐家托诺夫①学习小提琴演奏,而后跟随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到天津工作的安绍石老师学习钢琴、和声和乐理。1955年,季西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按时任副院长吕骥先生的安排,他先后跟随王振先、赵春峰、吴景略等演奏家学习民族器乐演奏,用两年时间打下扎实的民族音乐基础之后,才开始系统学习作曲
学习作曲期间,苏夏老师的作曲主课、姚锦新老师的作品分析等作曲理论课程都融入了对中国民族风格作品的分析与写作,使季西安在掌握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的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对西方音乐理论本土化的早期实践成果。同时,吕骥、马思聪、安波、赵讽、马可、李凌等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起到奠基作用的重要人物,都与季西安在学习或工作中有所接触,他们的思想和成果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学理积淀与价值取向的双重塑造,为其日后在中国音乐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学术研究领域坚定不移地走民族音乐道路构筑了根基。
(二)李西安音乐学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20世纪现代音乐观念的引入为中国专业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路径。尽管这一跨文化的音乐实践在当年引发了广泛争议,但李西安却以开明的态度积极声援“新潮音乐”。他认为,以谭盾、叶小钢、瞿小松为代表的青年作曲家将掀起中国音乐发展的巨大浪潮。
在1986年举行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即“兴城会议”)上,季西安发表了题为《走出大峡谷》的演讲,针对“古与今、中与外、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三组关系,结合中国音乐的历史脉络与发展现状,阐述了他对中国音乐创作和文化转型的深刻理解。此次演讲奠定了他日后提出的“张力场结构"的理论雏形。1994年,李西安在《文化转型与国乐的张力场结构》一文中完整阐述了“张力场结构”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对中国音乐未来发展大方向的战略构想,即以传统为根基,大胆融合现代技术,在多元性与创新中实现自我突破,探寻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三)李西安音乐学术思想的核心—“张力场结构”
“张力场结构”是指“在传统与现代这两极之间,构筑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传统与现代这两极间的张力与反张力的结果,其中间必然形成具有多层次结构功能与多元风格形态的巨大发展空间。两极的张力愈强,中间形态的层面就愈多,每个层面的适应能力与再生能力就愈强,整个张力场的包容性就愈大"②。在这一空间内,每个坐标点都具有其独特性,空间的两端向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延伸,也随着中与西、雅与俗的不同语境而变化。
例如,在音乐创作方面,一些作品在保持中国传统基调的同时,适度融入西方的现代技法,这是两极之间偏向中国的、传统的一类;而另一些作品则对传统音乐素材进行重构,以现代音乐语言为主导,这是两极之间偏向西方的、现代的一类。季西安用张力场结构概括了中国音乐作品各自的定位,并主张对张力场中的每一个层面进行更深挖掘和不断完善。
在宏观的音乐发展战略方面,李西安提出“保存要纯正,创作要大胆”的观点,既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明确指出现代观念的必要性,并且努力地拓展、深化张力场的两极。对此,他的解读为:“只有现代这一极已然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构成了对传统的强大威胁时,人们才意识到保存传统,特别是原样保存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只有深入地发掘传统,立体地把握传统,具备了强大的文化主体意识,传统才能成为新的创造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不但不为现代所惑,而且会从现代汲取新的养分,使古老的传统由静态转为动态,并最终抵达未来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