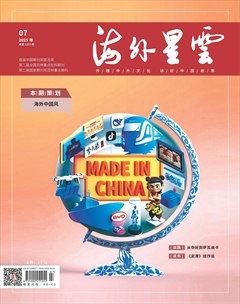在纸张普及之前,古人将文字书写在竹简与木牍上,合称为“简牍”。这些细长的木条或竹片,记载了泱泱华夏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甘肃简牍博物馆,珍藏着全国出土总数一半以上的简牍,共计6万多枚,其中汉简居多。当我的指尖隔着玻璃展柜轻抚那些沉睡的木条竹片,犹如看见两千年前的古人写给我们的信,字里行间不乏思乡之情与家国情怀,也隐藏了着许多故事和秘密。
寒冬玉门关,敦煌“军嫂”送棉衣
边塞烟火和敦煌的风沙,都曾打磨过这些古老简牍的棱角,如今它们温柔地躺在博物馆的玻璃罩下,墨迹斑驳。一枚木简的边缘裂开了细纹,上面写着:“元康二年,田卒张广贤,南阳宛人,左眉有痣,善制角弓。”田卒,是我国古代对屯田戍边士兵的称谓,这一制度起源于汉代。
恍惚间,我看见那个眉间生痣的河南青年,蹲坐在烽燧旁削木为弓,给战友们赶制守边御敌的兵器。边塞的月光洒在广贤的肩头,当最后一根弓弦绷紧时,他才在风声与羌笛声中,起身向沙漠戈壁中的营房走去。今天到此为止吧,做了一天弓累得腰酸手痛,该睡觉了。

在玉门关出土的三千多枚汉简中,戍卒名籍簿有 106 枚,这相当于汉代边防军的档案或花名册。简牍记载了他们的姓名,所属县、里,职务,年龄和特长等。
玉门关是汉长城西起点,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从汉武帝“开玉门,通西域”起,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当时谁在这里戍守?都留下了什么故事?答案就在一枚枚珍贵的汉简里。
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木简书信《儿尚与杨掾书》,记载的是写信人儿尚服役期已满,按规定应当有人来接替他的工作,但上级(尹府)迟迟没有下发遣返通知。儿尚归乡心切,恰逢杨掾要到尹府办事,便请对方上报他的情况。为了托杨掾帮忙,儿尚在信中先感谢对方曾给予自己的帮助,然后说尹府官员也会同情他这样的小姓贫寒人子。言下之意,只要杨掾肯帮忙,就一定能办成此事。简文中的“食尽乏”“数数哀怜”“小姓贫人子久居塞外”等,向我们展现出这位名叫儿尚的贫苦戍卒困守边塞 、无法与家人团聚的情形。
而在另一枚简牍上,还记载了汉代“军嫂”的故事:“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䜣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 ,这是玉门关的值守小吏广德和他的副手熹,向上级报备日常检查工作情况。
敢言之,一般是汉代下级向上级报告的用语。千秋燧,位于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西约 11公里处,是玉门关外规模较大的邮驿亭燧。寿陵里,敦煌县下辖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现在的村。
49 字的简牍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65年11月5日这天,家住寿陵里的女子赵负,赶来边关急切地说(“趣自言”意为急切地申说),她要去给时任千秋燧长的丈夫诉,送去棉衣等生活用品。“以令出关”的意思是,赵负依令取得了出关凭证。
两千多年前的寒冬季节,地处边塞的玉门关朔风凛冽、天寒地冻,戍边将士生活条件严酷,“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