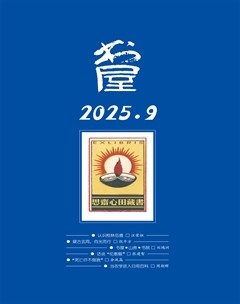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成绩优异,毕业后被选为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的院士,任期长达十五年。后于1934年受聘为英国研究院院士,翌年受聘为牛津讲席教授,至1941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辞职。后患脑卒中,于1943年英年早逝,只活了四十四岁,但著作已称宏富,学问涉及多领域。其《思想的历史》(The Idea of History)最为历史学界所重,书名一般译作《历史的观念》或《历史的理念》,题未洽文。此书尚未完成,柯氏身已先死,后由其友人根据遗稿编录增补而成,是一本对史学界影响很大的名著,传到中国,读者往往误解柯氏在主张“历史只是思想史”。已故清华教授何兆武曾对柯氏史学理论作了颇为全面的介绍,他传达柯氏之说为“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历史现象则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很精确地表达了柯氏的意思,但他也不精确地认为,柯氏引申之后,达到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怎么可能除了思想史以外没有别的历史呢?何氏也觉得没有理由将历史全部归结为思想史,但是柯林伍德并没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说的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举凡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都是思想的历史。
著名旅美学者余英时视章学诚(实斋)为中国的柯林伍德,虽受瞩目,但多误解。余氏认为乾嘉章氏与英哲柯林伍德所论有颇多相似之处,似是而实非,柯林伍德的主旨“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并非如余氏所谓的“将心比心,以己度人”。按,以今度古,何异强古人为己、强古为今,以为今心如是,古心亦如是,岂不荒谬?柯氏所说的心造,也不是“心心相印”,像韩愈赠孟东野所说“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或像刘得仁寄语其同志说“支颐不语相思坐,料得君心似我心”。诚如后史论者詹金斯(Keith Jenkins)所说,“同理心”(empathy)无法达成任务,因一人如何能进入另一人的内心?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有言:“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情景。”然而古今情势迥异,史料或散佚,或晦涩难解,比较容易依附自身所处时代,以今之学说推测古人的意志,难免流于穿凿附会而失真。道出将心比心之不易,类此诸说,都不是柯氏之意。柯氏所说别有旨归,所谓运作我心以重演彼心,并不是同情古人古事,而是古人古事由我心演古心,由我心知古心。如何能知古心?并非全凭主观空想,也不是各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去重演古史,中古的野蛮既不是远古的重演,近代的暴行也不是中古的重演,而是古人古事因史家的我心而重演。史家于重演之前,仍然需要先博览群籍,以文献佐证,知所取择,考信而后运古人古事于心,才能获知比较正确的历史知识。柯氏在《思想的历史》书中所说的“重演”,明言并非重申既往,而在史家当下的新语境中重演。重演一个过去的经验,或重新思考以前的一个思想。思想不仅仅是感觉,也是知识,使既往不至于消失,方能以今观古。古今虽然有隔,但不能否定两者之同,足以沟通弥合古今之间的时间距离,不全依靠残存的古物,而能够将古思因今思而复生。古人之思,可以重演于吾心,但所思古人之事,并非复制旧知,而是经由自身重演而得的新知。他的意思是,史家将往事置于胸中思之,是史家的重演,思想与所思对象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也是知识,所以史家之思是一种知识系统。史家重演古帝王之所思于心中,思考既往的经验,反思古时的经验。经验在前,反思经验在后,吾心是唯一的存在,为重演古人所必需。吾思他思,经重演而成吾思,吾思虽非原思,但古史已入我思。然则,古史乃今之表述,近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谓过去离不开当下的关切,也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涉及古今“视野的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柯氏同意伽氏所说:史家观古,离不开当下的视野。柯林伍德的重演之旨,亦在示法,其法就是要赋陈迹以新的生命。然而,所谓重演乃是理解历史的必要手段,史家自我做主,不拾人牙慧,所以历史不是古人古事的复苏,也不是原汁原味的“照本画符,重现原样”,更不是彼心如实的重现,而是史家经重演后的产品,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恢复往事,因非可奢求。柯氏承认出于人手的历史,不可能“尽而不污”(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但求“直不必尽”(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而已。
柯林伍德之说,明显与西方现代的实证史学异趣,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的新准则与方法。现代实证史学拟以科学方法观察与分类往事,柯氏以为不足,也不喜直书其事的记载,斥之为“剪刀与浆糊”的历史。史家剪贴信以为真的事实,而信之者又奉为权威,误导殊甚。柯林伍德认为实证的问题甚多,其中有缺漏、隐瞒、扭曲,甚至还有虚假的谎言。史家不能看到材料就写下来,因文献或文物未必是证据。柯氏以考古发现一块三角形的黏土为比喻,看来无关紧要,但可能是无声的言语,表达某种思想。柯林伍德要说明的是:每一行为有话可说,每一行为有思想可表。史家欲思古人之所思,便须结合事件与思想来解释史事。
柯林伍德崇尚唯心哲学,以思维为重,认为人事有异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没有思想,而人事唯思而后得之。所以柯氏坚持历史唯有从思想中得知。往事既逝,去留无踪,只留下残存的陈迹,史家重新思索已经泯灭的人事,才能获知比较可靠的历史知识。所以柯氏说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总结为“史事为史家心中之造”,也就是史家置往事于胸而后成史。若未能重演古人的经历,只能看到古人善恶的表象而已。柯林伍德认为史学家必须一再深思所要解释的思想,假如他做不到,最好收手,不必再做下去。柯林伍德指出,历史工作者长期以来只见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事”(res gestae),只对一些人事感兴趣。他说,人应在生物的基础上建立理性的自由行为,所谓自由不是出自生物本能,而为其自主理性建构,完全出自理性。所以已经发生的事,须由理性人的理性思考来处理。然则,欲知既往之事,唯有将往事一再由思想“重演”。柯林伍德指出:世间人事需要内省,有异于自然现象之需要外观。内省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解历史事件,须知事件背后的思想。因此,史学家研究历史人物,必须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概念、知识、推理、信仰以及计划等。他强调事件背后的思想,包括潜意识与非理性的思维。
章学诚的史意、史德,别出心裁,记言记事,以及思想史、政治史,皆属不同的范畴。章氏的史意是史事道德的内涵,史德是史家的心术,别出心裁是史家的创意,与柯氏重演之旨皆风马牛不相及。柯氏之意是,史事有内外之别,内在是“思想之呈现”(what is expressed);外在是呈现思想的“事件”(event)或“行动”(action),内外乃史之一体两面,无内不能知外,不知外无从知内。外在的行事须自内在的思想解释之。余英时说,内在是思想史,外在是政治史,去柯氏原意远矣。所谓思想史、政治史,在柯林伍德看来都是外在的事件,也就是他所说的“剪贴史学”。外者必须经由内在的思想来理解,才能获知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所以应该说是思想的历史,而非思想史。余英时教授视章学诚为“中国的柯林伍德”之后,遂说章学诚是传统中国唯一的历史哲学家。严格而论,中国并无类似泰西的历史哲学,章学诚没有必要与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拉亲戚关系,与黑格尔或汤恩比的玄学式历史哲学也形同陌路。章之《文史通义》一书中有不少命题,如“六经皆史”“朱陆异同”“道器合一”“经世致用”等,并未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作任何哲学的解释,更无建构大系统的论述。后人对这些命题,虽刻意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但有名无实,也未能替章学诚建立名副其实的历史哲学,也没有必要给章学戴上历史哲学的帽子。章、柯两氏心貌两不相同,中西学理有异,余氏将之比附,必然拟于不伦。
柯林伍德重演之说,评论者不乏其人,历史哲学名家如沃尔什(W. H. Walsh)评之为狭隘的理性史观,英国汤恩比(Arnold Toynbee)评之有理性而无感性,美国明克(Louis Mink)教授评之为个人主义的知识论,牛津教授加迪纳(Patrick Gardiner)则认为重演为史家深入理解古人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也有人认为,史家不可能重演古人所思,因今古时空不同,人也不一样。史家最多只能重演古人所思的副本,但柯林伍德有说:因今古之人虽然不同,但所用的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思维、同样的内容,故而古今时空之异并不相干。然则重演并不是史家有特异功能,如X光照出古人之所思,而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说:在用同一语文的情况下,可从文字表达的意义去理解;然而,重演之旨要在今古同一思维中运作。读柯氏之书,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重演好像是将心比心的反思,但此一印象并不正确。思古人之所思,古人思想固然可以重思,但感情又如何再思?他在《历史原理与历史哲学论文集》中有补充说明,认为古人的情绪与非理性思维固然难以捉摸,但无论理性的思想还是非理性的感情,都需要证据来确定。史家重演并不是自由心证,而须慎思明辨,所以仍需文献考证,根据证据释史。柯氏强调重演只是理解历史的方法,也是史家应有的自主权,历史毕竟是史家的著作。重演既有语文作为媒介,史家可以借社会成规与传统习俗来增加对历史人物行为的理解。当历史人物的社会准则不同于史家之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史家的一些设想每基于已有的设想,如视某人为土匪,此认知是基于先前对土匪的认知,柯林伍德称之为“相对设想”(relative presupposition)。至于绝对的设想,便无预先的设想。绝对设想有复杂的意结,规范今人的行为,复杂的意结所构成的语文及其意义,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紧张的、矛盾的,当紧绷得太厉害时,整个体系便会崩溃,然后由另一体系取代,近似库恩(Thomas Kuhn)的典范转移说。所以绝对设想不是武断的惯例,而是明确的选项。史家未必能清晰而详细地说出古人行为的准则,但至少应知历史人物是否遵从准则。柯林伍德并未告知预设决定行动到何程度,他也许认为,相对的预设会给史家更好的想法,他视自我认知为人类的本能,由自我认知自己预设的形成,另以既有的预设增益自我的认知,相对的预设未必尽善,但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总而言之,柯氏对史学求真的看法仍然是乐观的,有异于后现代史家的悲观。对柯林伍德而言,研究历史不是余兴,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他说:“莫问我是否是史家,要问如何成为好的史家。”近年柯氏遗稿频出,对他理解更深,方知其学绵密丰富,所提出的问题值得严肃看待。
柯林伍德过早离世,未及见后现代主义风潮的兴起,不知其如何应对。唯其师承者克罗齐,崇尚唯心,强调历史思维的重要,要旨可归纳如下:一则曰,历史乃是“思想的历史”,不是思想史,因历史犹如过眼烟云,不复存在,不能如眼前实物之可见,只是历史思想里的烟雾,有待澄清,所以历史知识乃思想的产物,历史叙事亦即史家的心中之造;二则曰,所谓心中之造,乃史家将往事置于胸中,含英咀华而后发为文章。柯氏论及胸中之造,重演古王的经验,可以呼应宋人吕东莱所说“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若合符节,可惜吕氏仅点到为止,未多申论。明末王夫之(船山)亦有言:“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船山也能发柯氏的先声,亦惜止于论点,而未将论述展开。清人龚自珍(定庵)所作的比喻“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也能略发百年后柯氏“重演”的先声。定庵更进而强调:能入需要“实录”,仅凭“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言“必有余呓”;善出需要“高情”,否则史家又如何能代言优人之“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则史言“必有余喘”。定庵要求史家“毋呓毋喘”,就是要说得周延完备。定庵尊史尚有余义,如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并以老子为柱下史而为道家大宗为证。换言之,应由史实引出理论,而非以论带史。但是定庵论史亦点到为止,若加以申论,大可开发为一历史哲学。钱锺书诠释重演之法,最为精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于此可以确定,柯林伍德所谓“重演”,意在批判性之反思,历史乃史家的作品,加重史家在史学上的重要性。史家并不能全靠主观玄思,仍须依赖历史证据,史料仍然不可或缺。所以柯氏之重演,是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史家必须自我做主,呈现自家的主体性。他认为任何历史事件或行动都有内外两面,外在事件与内在思想乃历史知识的一体两面。柯林伍德曾批评古代史学名家塔西佗之《罗马史》仅仅以善恶来评价历史人物,正因史家未能于其内心之中重演古人的经验,所以只见古人外在所表现的善恶而已,未免偏颇,故而史家必须思罗马君臣之所思。换言之,若欲深知刘、项楚汉之争,不能仅见鸿门宴、十面埋伏、乌江自刎等外在表象,也应一究引导刘、项二人所作所为的思想,包括情境、意图与决策等错综复杂的内在心理因素,绝不能仅以普遍法则绳之。
柯林伍德说史学是科学,别有所指。科学应指自然科学,科学不必去收集已知的材料而后安排之,而是去寻找未知之事而后发现之。但史学旨在发掘既往的人事,发现问题,去找解答,可见柯氏心中的科学只是“有系统的知识”。所以,他绝未将史学与自然科学画等号,也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古人的理性言行。属于人文的史学与属于自然的科学本质有异,并非柯林伍德的创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早已言之。他说科学需要“解释”(Erklaren),而历史需要“理解”(Verstehen),取径不同。自然科学观今,历史学科观古,两者性质基本不同。然则,欲将史学科学化,遂被二十世纪美国史家赫克斯特(John H. Hexter)讥为“精致的呓语”(sophistical flimflam)。柯林伍德更进一步说,史学家不仅要发现史实,且需知道史实背后的思想,再经思想了解史实,才能知史实如何发生。史家再思古人之所思,理解古人之所思,可明一代之史,而后分析之、叙述之,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才是史家所应优为者。史家并非不求因果,只是历史因果有异于科学,史无完美之因,史家既多,而视角各自不同,所见之因,繁多而又迥异,仅可称之为“相对之因”(relativity of causes),与史实相关而非必然。所以,历史不能借自然科学方法,历史人物的内在思维无法如实物一样可以观察,历史事件随风而逝,也无从目睹,故而柯氏认为史家必须有其历史想象,根据史料,经由重演之法,获知有效的历史知识。
柯林伍德之最终目的,还是要追求比较信而可征的历史知识,仍持乐观的态度,与后现代史家以为历史真相不可求的悲观立场绝不相同。不过,柯氏以思想与想象为求真的载具,自维柯以来,凡重视精神境界的西方哲人,多认为思想与想象区别不大。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均致力于人生活动的认知,同样以当今之观点建构意义,故历史与小说皆属当今,皆由当今之想象创造人生。以此观之,就思想与想象而言,史学家与小说家在运作上并无差异。既然如此,岂不将授后现代理论家以柄?不过,柯林伍德力辩史学家与小说家并不相同,史家与小说家之任务,固然都以叙事述景为务,展示动机,以分析人性为要,操觚时意由己出,不假借他人,都属于“先验想象”(á priori imagination)的行为。“先验”概念出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认为没有任何知识可以超越经验,然而部分先验知识不由经验推论而得,故先验之见并非植根于经验,而存在于抽象的推理之中。经验之知得自感觉,乃“后验”(á posteriori)之知,而先验之知则得自“理解”(understanding)。若用之于史学,从经验获得的知识,无论耳闻或阅读皆属感官的认知,认知到史实之存在属于后验。理解史实而后成为历史知识,则有赖于思想,属于先验。例如圆明园之焚毁为经验认知的史实,而其之所以焚毁、如何焚毁则是理解后的历史知识,属于先验。故柯林伍德认为,从先验的层次而言,史家与小说家并无不同,皆具独立于经验外之理解,但是真正的区别就在经验事物的虚实,史家必须传真,而小说家可以言虚。然而史家所理解的,必须是真人实事以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必须服膺三大准则:其一,所叙之事必落实于时地;其二,必须前后一致;其三,必须涉及实证。此三大准则小说家皆不必遵循。正由于史家为史学之准则所限,故其思想里的历史世界有一无二;而小说家既无所限,想象之文学世界可以无限。质言之,历史与小说叙事虽同,但目的迥异;历史不能无中生有,史若不实便成秽史;小说言虚,反增情趣,不仅是作者之初衷,亦读者所期盼。然则历史与小说两者绝然泾渭分明,不可如后史论者将其混为一谈,足可破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史即文说。
后现代史学今不能通古之论,柯林伍德必不以为然。若谓:“每一个当今皆有其过去,每一由想象重建的过去,皆以当今之过去为目标,而当今之中,思古之想象绵绵不辍。”又尝以流水比喻历史思想的稍纵即逝:“举足涉水,所涉之水少焉即逝;再举其足,已非前水。”谓史家不能一劳永逸,须尽全力与日俱新。重建古史固然有其难度,史证、史法、史释皆与时俱变,故每一代史家皆须重写历史。柯林伍德论史,主张今可知古,昭然可见。所要说明的似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乃史家自身之创作”的史无定论,但柯氏并未落入后现代理论家之口舌,柯氏创作所根据的重演之旨,并不认同海登·怀特之说。
柯林伍德又说,所有撰述无不反映时代,诗道尤其如此,因人由其生长的世界所形塑,其人的诗感,使其心物合一,天人相应。历史乃在时空之中的行动、才性、氛围、精神,所展示者乃既往的情景,而非抽象的通则。故德国诗哲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直言:“历史根本就是诗,只留下一则似是真正发生过的故事。”诗道讲究妙悟,实为才识超迈的泉源。史家内夫(Emery E. Neff)以《诗之史》(The Poetry of History)为其书名,谓诗乃“人类精神要素最完备的象征”,乃史家致知的最佳选择。史著具有诗质,不仅仅叙事而已,尚能唤醒遥远的时代,使之重现,如劫灰之复燃,重现其神采,始足以动人心弦,不仅传真,更能传神。柯林伍德曾引麦考雷(Thomas Macaulay)之名言说“完美的史家必具丰富的想象力,足以使其叙事生动感人”,意犹未尽,更推而广之,认为历史想象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历史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史家若缺乏想象力,则其叙事必然非常寒碜。
柯林伍德的《思想的历史》与卡尔的《何谓历史》(What is History)中文翻译本约略同时出版。柯书要求史家能赋既往的陈迹以新生命,如钱锺书所言,“必以今心裁择”,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性。卡尔与柯林伍德一样,都要将史学的重心从史料移到史家,不取绝对的客观论,似乎为相对主义以及后现代史学铺了路,但柯、卡两位所要强调的仍是通过“证据”与“客观”,以便重建既往的真相。换言之,两人都将重建往事的重责大任赋予史家,而后现代理论则否定史家有担此重任的能力与可能性,认为根据原料演成的证据,并不能直接通往既往,只是用文字建构既往,若想单凭客观重建既往,将是妄想。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为人类认识自己而提供知识,之所以重要,端因人类有此需要,不仅要知道特殊的个人,也要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然而认识自己,先要知道何以为人,要知道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自知而后能知力之所及。若不试之,不知力道的轻重,必须试而后知能耐的强弱。然而,历史的价值无非记录人事,读史所以知人。
柯林伍德以历史哲学闻名于世,因其兴趣至广,多有跨领域的成就。他的美学研究追随克罗齐,认为艺术主要表达感情,艺术家的社会角色要能清楚表达自治小区的感情。他的政治哲学要维护欧陆的自由主义,各自治小区能自由表达政治意见,尽量减少异见。他在考古学上受到父亲的熏陶,也有所建树。他在牛津大学教哲学时,曾趁长假去做考古工作,研究罗马帝国在英国边疆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并多次参与发掘,发现此一古城墙并不是作战平台,而是哨兵走廊。他于1937年最后一次从事发掘,有关亚瑟王的“圆桌”(Round Table),传说王以圆桌使其武士座位无分高下,以示平等。柯林伍德的考古,对象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他虽未对新石器时代的活动有任何肯定的结论,但毕竟发现两根石柱的底座、近似火葬的沟槽,以及若干柱孔遗物。随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无法继续考古。他对英国考古学最大的贡献是坚持他的“问答考古学”(Question and Answer archaeology),也就是说:除非有需解答的问题,不必去考古发掘。他无疑是研治罗马帝国时代英吉利的权威学者之一,更鲜为人知的是,柯林伍德还是很好的散文作家。他曾出版一本游记,记载他与几位学生在地中海帆船航行的乐事。世人多惜其不能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