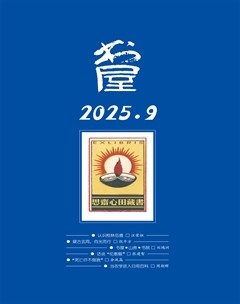由万俊人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吾道文丛》书系,专以名士大家的学术自述为对象。目前已出版数种,本本精彩,绝对值回书价,分别是钱理群《老了,老了,还在求索》、成中英《我的治学渊源和精神》、郭齐勇《返本开新》、冯天瑜《跬步千里》、赵汀阳《方法与问题》,其中也有汪荣祖《庸椽楼记梦》。
汪荣祖先生出生于1940年,安徽旌德人,生于上海,长于台湾,主要任教时间在美国。他在《庸椽楼记梦》中自言,本无写回忆录的想法,因缘际会,中华书局精印了《云雏记事诗稿》数百册为寿,其后又得《湘水》主编黄友爱邀稿,于是回首来时路,记人、述事、说前尘、谈学术、论史学,遂有《庸椽楼记梦》。
本书除《弁言》与《附录》之外,还有九章,每章各有一位或数位主题人物,对汪荣祖有着不同的意义,如诗缘、文字缘、同窗、同志、师恩,等等,有中有西。此类“掌故”,来源于汪荣祖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人或长或短,记事有略有详,文笔却都典雅精致,每读完一段或一章,仍有余韵。而书中争论之学术观点、彼此的政治立场,更是交织成思想激辩与叙事选择并存的“知识史”,让人如入“万象真藏”中,目不暇给,时而感怀薪火相传之情深,时而惊异观念交锋之激烈,既有学人间的“隐情私衷”,也有前理解的“先入为主”,读来如登山,层峦叠嶂,各见风景。
《庸椽楼记梦》所记人物,以及与汪荣祖的交游经历,多散见于汪荣祖其他著作,此处重编、重写,更能让读者较全面、有系统地阅读并理解其人际网络与学术观点。汪荣祖从少年时的诗缘谈起,先讲吴博全,再谈叶嘉莹,又从毓老说到子老,以及萧公权、何炳棣、钱锺书、周一良、唐长孺、黄永年、蒋秉南、杜维运、余英时、李敖、章念驰,等等。第四章《海外中国学者第一人》,篇名为杨联陞推许萧公权之语,汪荣祖与老师萧公权相聚五年,鱼雁往返十年。汪荣祖在美国读书与任教期间,史学界正逢社会科学主导,急于提出诸多解释模式与理论。萧公权反其道而行,强调“放眼看书”以及“小心抉择”,认为“没有扎实基础的理论与模式,虽赢得一时的赞赏,得到升迁与加薪的实惠,何异沙滩上的城堡,随潮落而消逝”。又提及萧公权著作虽已有中译本,始终不全,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立志要将《中国政治思想史》译成英文,终究未成,“萧牟二师均有憾也”。至于第三章《天涯存知己》则是记与外国友人,如霍博(Paul S. Holbo)、屈莱果(Donald W. Treadgold)、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麦可侯斯(Michael Hurst)等通信论学、互赠著作。汪荣祖曾任屈莱果助理多年,特别欣赏他对殷海光的仗义援手;与牟复礼亦师亦友,也共学适道;霍博指导汪荣祖写作硕士论文,专长是美国外交史;麦可侯斯对十九与二十世纪英国史尤为娴熟,与汪荣祖很谈得来。“我流寓北美约四十年,其间师友多不胜数,但印象深刻,长期保持联系、鱼雁不断的很少,特别难忘的洋师友有三位(按:应该是四位,三位为笔误)”,他们都与汪荣祖有着深浅不一的缘分。
其中陈寅恪最为特别。就像余英时从没见过胡适一样,汪荣祖与陈寅恪缘悭一面,却与其后代、学生、相关研究者颇有过从,这就是第五章《义宁文字缘》所谈。1976年,汪荣祖出版第一本著作《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因当时书籍流通不易,“所以我借这本小书作为结识许多陈门弟子的桥梁”,同时也结识了“陈寅恪的三个女儿与著名的国内外学者”。增广见闻,温故知新,于是在1984年增写此书,因收入评传丛书,主编者改书名为《陈寅恪评传》。后出的北大版与增订的台北联经版仍用《史家陈寅恪传》书名,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最新增订本亦然。当然,汪先生因陈寅恪晚年境遇引起的笔战亦不少,其中与余英时的论辩最为人所知。
除了陈寅恪,《余杭文字缘》一章还论及章太炎。汪荣祖主要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入手,进而发现章太炎隐有“文化多元论”的倾向,他的《齐物论释》,讲齐物,说平等,其实是在讲多元万殊的合理性,不同文化都有其价值,这才是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