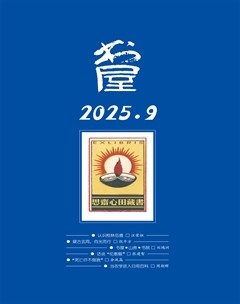我的这本书,有的地方写的不够详尽,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批评。……这是“狮子搏兔”的工作,是用过全身气力的,几十年来断断续续,不知费了多少工夫。想知道读者了解到那种地步。
1988年3月,徐梵澄先生《老子臆解》一书付梓。遗憾的是,该书问世后并未引起较大反响,以致梵澄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有此怅然之叹。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此书可以说是倾注了先生的全部心力,自信可以传世。
“那么先生认为自己可以传世的是什么呢?”
“《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可以算是吧。此外《老子臆解》,有二十三处,发前人所未发,也算有些新东西。”
这段对话发生于1992年12月28日,系先生与友人谈及“人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可以留下的东西”时所发之感慨。先生认为《老子臆解》发前人所未发,可以作为自己的传世之作。中国读书人历来追求“三不朽”,先生在阐发老子“死而不亡者寿”一句时说道:“今言‘精神不死’。春秋叔孙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身殁,其德、其功、其言在后世不忘,可谓不朽。不朽,寿也。”梵澄先生欲以立言传世,求其精神不朽,虽为解老,亦是自期。
该书所产生的反响与先生的期许远不相侔,自问世至今,仅有孙波、王鹰、梅文辉三位先生有所论及。诚如尼采之言“我的话是说给二百年后的耳朵听的”,可谓道出了古今诸多哲人的遭际,尼采如是,船山如是!在我看来,该书乃至先生的其他著述未引起较大关注,原因不外有二:一则,先生治学属传统路径,与今天的专业化取径不同,秉持“学问主通不主专,贵通人不尚专家”的治学门径,使得今人接触这一宗学问时如同面对一个“铁馒头”,不知从何处下嘴;二则,先生文字简洁,往往“解明书中之义理,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加之,此精神哲学属“内学”,非证悟精神真理不能有得,而今人多驰骛于外,与此有隔,遂不能契入。不唯人择学问,学问亦择人,此宗学问清寂,盖俟有心人也。
孔子言:“必世而后仁。”梵澄先生示寂已二十五年,所谓时移世易,如今精神道大放异彩,相信必有更多同人沿着先生的足迹继续跋涉。若此,则一切文字障碍皆不成问题,正如先生指点友人读书时所言:“来信说《五十奥义书》中有不解处,我相信其文字是明白的。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脑中灰色质上增多了施纹或生长了新细胞),理解力增强了,再看又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明’是生长着的。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便可离弃这书,处在高境而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不可。这于《奥义书》如此,于《人生论》亦然。书,无论是什么宝典,也究竟是外物。”
“通常介绍某种学术,必大事张扬一番,我从来不如此作。这属于‘内学’,最宜默默无闻,让人自求自证。否则变怪百出,贻误不浅。”因此,吾人不是与梵澄先生有隔,而是与自求自证之“内学”有隔。中华学问,仁智双彰,功夫境界,一体两面,今人逞其智而遗其仁,此阿罗频多谓尼采“半盲的见士”,吾人所深鉴也。
梵澄先生自道《老子臆解》有二十三处新见,可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那么我们如何窥得门径呢?或许正如先生在翻译尼采时所作序言:“在旅行的长途中偶尔发现一两片小标志,指示前人曾此经过,则当能更有勇力前行,而且突过以往的限度。”令人欣忭的是,此“标志”在序言中仿佛可见:“然帛本一字之殊,固宜珍若璆琳者也。……析理参以《周易》及先秦古说,不废《庄子》;偶见颇同西洋哲学者,标出之,意在点染以时代精神;无所发挥,盖非论老子哲学也。隶事,多取《春秋传》,间有取后世者,皆历史大事。音义多本之《尔雅》《诗序》《说文》等,以古字义解古文义,亦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者。”是故吾人只需沿此途辙前进,便可略窥老子“超上哲学”的精神畛域。
一字之异,儒道殊途
梵澄先生的《老子臆解》与寻常《老子》注释不同,主要分考证、臆解两端,只撮其大意、疑难进行疏释,无分章析句之烦琐,可谓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兼顾,颇得桐城遗风。今本《老子》第十四章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梵澄先生从帛书甲乙本判定为:“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