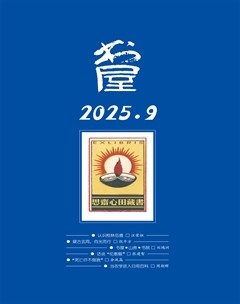1887年9月12日,鲍山下的小港里自然村,钱氏祖屋东侧阁楼里传来一阵清脆响亮的啼哭声,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字音韵学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钱玄同(1887—1939)就这样诞生了。
此时,他的兄长钱恂已有三十五岁,早已声名在外。这位晚清著名外交家兼思想开明的学者,已经同迁居海宁硖石同样开明的单士厘共结连理,并于三个月后生下大儿子钱稻孙。父亲钱振常已六十二岁,他早就从北京辞官,先后辗转浙江、江苏等省,在绍兴、杭州、扬州的几个书院以教书为业,在绍兴龙门书院曾教过蔡元培。
身体的健康与否对生命个体成长中的性情与发展影响颇大。钱玄同从小身体就很羸弱,且不爱运动,经常生病。当我们细细翻阅钱玄同的日记时,不难发现这几乎是一部从小开始与病魔作斗争、极其不易的个人成长史:失眠、多汗、发寒热、神经衰弱、视网膜炎、心血管病……他不跑,也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会跌一跤,四十岁过后就要使用手杖。在日本留学期间,长兄钱恂曾带领一家人外出郊游,连裹着小脚已四十多岁的长嫂单士厘都积极愉快地体验着登山的乐趣,可二十岁的钱玄同却躺在旅馆的榻榻米上发寒热。他的长子钱秉雄后来回忆父亲时写道:“他年轻时,晨起常用冷水低头冲颈部后端,常服西药‘拍拉托’来治疗神经衰弱。”
钱玄同的肉体时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困扰与折磨,还因健康受限而未能像常人一般游山玩水,敞开身心去体验诗和远方。一直以来,他还承受着严厉的家庭教育,令他的成长经历与众不同。当其他同龄孩童正撅着屁股玩泥巴、围着桌子追逐嬉戏时,钱玄同却被关在家中要求勤奋苦读。三岁时就开始随父亲背诵《尔雅》,五岁时则开始上私塾学读经书。有一次钱玄同偷看经文之外的戏本《桃花扇》被私塾老师发现,早经他父亲授意要严加看管的老师脸一沉,手一抬,一把戒尺立即破风打来,“啪”一下,在钱玄同的眉心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铭刻了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然而,父亲对钱玄同严加管教直到十二岁,给儿子打下了治学的童子功,旋即撒手人寰。钱玄同十六岁时,母亲也病逝了。长兄如父,于是钱玄同就成了长兄和长嫂悉心照顾的对象,他与同岁的侄儿在同一个环境里一起长大。钱恂是晚清能干的外交人才,曾将大量的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对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都有较深造诣。他自己最得意的是家传的音韵学。受长兄影响,音韵学后来也成为钱玄同最主要的治学方向。
疾病缠身使钱玄同极易狂躁,容易激动和情绪化;但严格的家庭教育又让他极具内涵修养,稳重而恭顺。如此对立矛盾的人格,也让钱玄同一方面积极地向光前行,冲在前沿,敢为人先,成为摧枯拉朽的文化斗士;而另一方面,光照留在他背后的黑影也一直随行,他始终是恭敬和顺的孝悌弟子。
一
1903年,钱玄同将过去的人生逐渐关闭,逐渐打开面向未来的门窗,渴望接受新的事物,改变陈旧滞重的生活状态。十七岁那年的冬天,同乡朋友方青箱送给他两本书: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他读完以后,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以前的“尊清”见解开始有所动摇。次年,他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毅然决然地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还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湖州白话报》,报头上只写“甲辰年”却不书“光绪三十年”,以表示反对清朝的决心。然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前,他突然主张革命以后应复古礼,还写了一篇《深衣冠服说》,并做了一套复古的礼服穿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