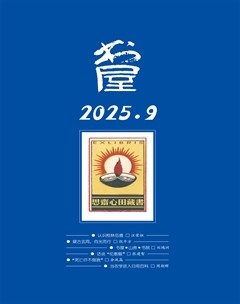民国时期,大学实行自主招生政策,各校在考试命题上尽显神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文题,更成为展现学校风貌的重要窗口。
一派明确要求作文只能用文言。如1933年、1934年的中央大学,特意在题目中写明“体限文言”,或如1933年的北洋工学院,让考生“注意”“须用文言”。其他更多名校的作文题,虽未明示只能写文言,但其题目多是“语谓‘多难兴邦’,试申其说”之类,像是要求作文言文的意思,且因思维定式,考生写文言更顺当。
另一派明确要求用白话文。这在当时尚属激进,据目前所见资料,全面抗战前的国文试卷中明确要求“作白话文”的,仅见北京大学,未免形单影只。其实施年份也不算太早,1932年的试题中尚无此要求,1933年因资料缺失,如何要求尚不明确,1934年及其后两年,都要求“作白话文”。这体现的应该是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适的主张,他认为高中毕业生亦即大学投考生,应能运用白话文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而无文法错误。至于文言写作,只适用于特殊人群,即“有天才高且熟于文法者,宜鼓励古文作文”。
不过,胡适的主张一旦落实到入学考试中,将给那些不会白话文写作,或更惯于文言写作的考生带来影响。1934年,严复的长孙女严倚云想报考北大,又担心“没有写过白话文”,犹豫不决,后经人劝说投考,“谁知道我给撞上了”。就这样,她也被录取了,也不知她怎么写的作文。
清华的作文试题则介于两派之间,自1931年以后,每年考题上都会专门加六个字“文言白话均可”。这一中间路线也与教育部的要求相吻合。1929年8月,教育部制定了《高级中学普通科暂行课程标准》,就国文方面,要求高中毕业生需达到几条最低限度的标准,其中之一即“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字”。后该标准于1932、1936年两次修订,然此项要求未变。
虽然标明“文言白话均可”,然投考清华的学子中,写白话者占绝大多数,写文言的只有一小部分。如1933年的考试,据阅卷人朱自清估计,“作文言的很少”,有时甚或少至极个别人。据语言学家吴宗济回忆,1928年他考清华时,所有考生里面只有两个人用文言答卷子,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是后来成为水电工程建设和规划专家的覃修典。这固然反映了文言在考生心目中地位的衰落,也与清华作文题目潜在的导向性有关。比如1934年的题目之一“夏日的昆虫”,1935年的题目“我的国文教师”及1936年的题目“我的衣服”,着一“的”字,不写白话不对味。若题目作“夏虫”“余国文师”“吾之衣”之类,估计作文言的会增加不少。因为当时的考生中,许多人是白话、文言两手都练,以备应考具有不同要求的多所大学。就此,有成功考取清华的过来人建议道:“关于国文的做法,当然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文言或语体;不过最好还是用语体,即所谓五四的新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