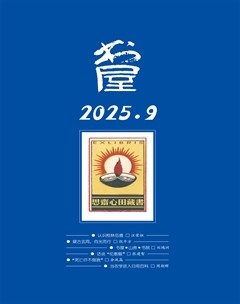梁漱溟的性情有几分狂傲,自视甚高的他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也不是完全“目中无人”。朋友当中,有不少人是他心里折服而尊敬的,而且“他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价值”。“价值”不同,“重量”自然不同。如果硬是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梁漱溟说,“伍庸伯先生应该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更无人能相比并,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应该亦说是最亲近的和相当深的”。
伍庸伯(1886—1952),名观淇,广东番禺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1916年,而立之年的伍庸伯毅然辞官,求学于京。1919年,新思潮逐步高涨时,伍庸伯几乎每日前往北大旁听。正是在这一时期,梁漱溟与伍庸伯相识。梁漱溟回忆:“我与伍先生相识于民国八年在林宰平(志钧)先生家。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印度哲学讲席,伍先生主动要林先生作介绍,意在问佛学于我。第一次见面谈话,在彼此问答之间,并不投契。却是我深觉他人的气味好,心生敬慕,留有印象不忘。隔了许久,我自动访他谈学,才渐多往来。”
梁漱溟比伍庸伯小七岁,一个在北大授课,一个在北大旁听,可谓身份悬殊。但两人的交往并未受此影响。实际上,伍庸伯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博闻强识,行不苟合,在京求学一段时间后,“就出其心得者为朋友们讲说”。作为主讲人,伍庸伯给同乡学友讲书,所讲包括《大学》《中庸》《孟子》等。1920年间,伍庸伯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中讲学,梁漱溟也听过两次。伍庸伯立身行事恪守“言忠信,行笃敬”的信条,梁漱溟特别钦佩。对于伍庸伯的讲学,梁漱溟日后回忆:“他原非为讲书而讲书的。他要走的道路既定,其他学问道路便绝口不讲(亦少见评论);为人讲说时,除与《大学》相发明的古书文外,亦从不去谈它。”
1921年8月,伍庸伯回广东前,还做了梁漱溟的媒人。此前,年轻的梁漱溟一心向佛,无意于婚姻和家庭。执教北大后,人生态度渐渐转变,对谈情说爱、结婚成家也不再抵触。一日,梁漱溟正伏案写作,伍庸伯“忽枉顾”,表示愿将自己的妻妹黄靖贤介绍给他。当问及择偶标准时,梁漱溟似乎毫不在意:一则不从相貌上计较;二则不从年龄大小上计较;三则不从学历上计较(不识字亦无妨);四则不需核对年庚八字。梁漱溟声称“殆无条件之可言”,却“非尽人可妻”。他心目中“悬想得一宽厚和平之人”,又希望对方“意趣超俗”,而“魄力不足以副之,势将与流俗扞格而自苦”,所以还要有“魄力”。面对梁漱溟的“既要”“又要”和“还要”,伍庸伯笑答:“你原说无条件,你这样的条件又太高了。然而我要为你介绍之人却约略有些相近。”是年,在伍庸伯的撮合下,梁漱溟与黄靖贤结为连理。梁与伍在知交之外又多了一层连襟关系。
伍庸伯回到广东以后,有意整理乡事,如平息械斗、肃清盗匪、兴办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