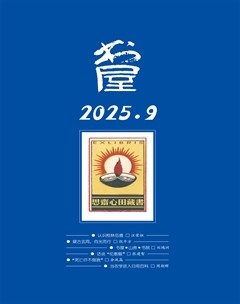金九经,1899年出生于韩国庆州,传说庆州金氏始祖诞生于鸡林,故自号鸡林。1921年在日本京都大谷大学预科学习,后转入文学部中国文学科。留日期间,金九经师从日本汉学家铃木大拙、内藤湖南、仓石武四郎,以及避居日本的中国佛学家夏继泉等,学习禅宗与汉学,对汉文化逐渐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金九经结束留学后,在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不久,他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执教,并活跃于北京文教界,与鲁迅、魏建功、胡适、周作人等交游,形成奇妙的“朋友圈”。
金九经与鲁迅
金九经来到中国的确切日期难以考证。李霁野在《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中写到鲁迅1929年5月自沪返京时,曾三访未名社,正好遇到临时借住于此的金九经:“那时有个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逃到北京的朝鲜人住在未名社。”鲁迅与金九经因此相识。
文中还写到鲁迅与金九经的谈话场景,表现了鲁迅对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关注与同情:“先生极为关心朝鲜的情况,同他谈了很久,并为他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谈话时鲁迅先生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对待民族问题,一方面希望弱小民族通过斗争得到复兴,一方面极为憎恶大国沙文主义,所以对这个朝鲜人极为关怀并同情。”另据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文,鲁迅对为金九经题写扇面非常谦虚,表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怕把很好的扇面糟蹋了”。可见,这幅扇面是由金九经持来并请求鲁迅题诗的。
此外,李霁野在《关于鲁迅先生的日记和手迹》中的一段回忆可以补充鲁迅与金九经在未名社会面的细节:“鲁迅先生1929年5月回到北京省亲,他在日记中写道,曾三次到未名社,25日‘往未名社谈至晚’。当时有一个朝鲜人,因为不满意日本人的措施,脱离了日本人所办的大学来到北京。一时没有办法,就住在未名社。鲁迅先生和他谈了很多话,主要是了解朝鲜的情况。”
在这趟二十天的回京行程中,鲁迅日记记载了三次与金九经的会面。5月31日:“午后金九经偕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象拓本。”6月2日:“夜金九经、水野清一来。”6月3日:“携行李赴津浦车站登车……金九经、魏建功、张目寒、常维钧、李霁野、台静农皆来送。九经赠《改造》一本,维钧赠《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一本。”
其中5月31日的会面,在场者之一的仓石武四郎在《鲁迅的追念》中写道:“那时候,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中有一些对考古学有兴趣的朋友,希望访问鲁迅先生的家。为此而拜托那位朝鲜语讲师,我也希望加入这些朋友的行列中。讲师先生看上去似乎有些为难,他认为让鲁迅先生为几个少数人而停笔,有些不好办。我们这些在北京大学的日本听讲生,原先在日本也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了,终于,我们大家就一起去了。”所谓“那位朝鲜语讲师”就是很快在北京大学执教的金九经,另两位同行者冢本善隆与水野清一是在北京从事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日本学者。
仓石武四郎在文中还写到,此行目的是观赏鲁迅所藏的六朝造像拓本,与鲁迅日记所记一致,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关于鲁迅如何保存拓本的回忆:“考古学者们之所以访问鲁迅先生,是因为先生收藏了六朝造像的拓本。在鲁迅先生家的一间屋子里,先生把几种类型的拓本拿给我们看,使人惊奇的是先生的保存方法,据说北京大学的拓本全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拓本都有衬里,有不少是鲁迅先生自己亲手做的——用很整洁的裁剪得一定大小的纸做成衬里,所以拓本一点儿也没有损坏。因为衬里裁剪大小一样,每一个拓本的大小也就一样,所以整齐地叠在一起,寻找任何一个拓本都可以很快地把它抽出来。鲁迅先生说,这些造像几乎都是河北地区的,有一个是江南的东西。他拿出几份拓本说是送给我们,每人一份。”
6月2日,金九经与水野清一再次拜访鲁迅,应还是为交流中国古代造像艺术。从鲁迅6月3日日记所记来看,金九经是送行小队的牵头者,他赠送给鲁迅的《改造》是日本改造社所出的日文杂志。
6月21日,回到上海后的鲁迅在给李霁野信中写道:“在车站上别后,五日午后便到上海,毫无阻滞。会见维钧,建功,九经,静农,目寒,丛芜,素园诸兄时,乞转告为荷。”在他请求转达平安讯息的对象中就有金九经。此后,鲁迅日记再未有对金九经的记载。
金九经与魏建功
在金九经率领的送行小队成员中,鲁迅首先提及的是魏建功,这并非偶然。金九经与魏建功交游深厚,两人相识于朝鲜。1927年4月,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魏建功受校方委派,赴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担任中文教师,其时金九经在该校图书馆工作。魏建功不通朝鲜语,遂请金九经一面教授自己语言,一面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便宜,两人由此开始了交往。
1928年8月,魏建功结束在朝鲜的教学工作,回到北京。因不满京城帝国大学处于日本人治下,约在1929年,金九经携家眷自朝来华,由魏建功介绍居住在未名社。也因魏建功的举荐,金九经不久后在北京大学教授朝鲜文和日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