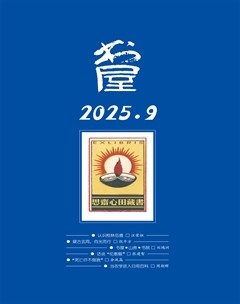一
1925年11月,在郭松龄反戈张作霖的战役中,林长民不幸遇难。林长民去世后不久,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撰《伤双栝老人》一文纪念,发表了林长民的书信《一封情书》并作按语。在文章中,徐志摩自称“忘年小友”,他的悼念文不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来写,而是着眼于伦常亲情,感情浓烈,直抒胸臆,充满悲惋的情绪,从中可见他与林长民不一般的友谊。
林徽因很少谈到父亲和徐志摩的友情,在纪念志摩的文章里,她亦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林徽因很明白地承认,她的父亲和徐志摩是知己,然而一笔带过,没有展开。
正如徐志摩在《伤双栝老人》中所写,“早年在国外初识面”,他和林长民初识于英国,时间大约是1921年1月。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徐志摩回忆了他结识狄更生的经过,其实也是与林长民订交的过程。初见是在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上,再次相见是在伦敦林长民的寓所。林长民有几封致徐志摩的信,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中,其中有一封短函,即邀请徐志摩来寓聚会。
林长民与徐志摩相识之后,一定有相见恨晚之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的人生有很多的交集,且说三点。其一,梁启超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林长民与梁启超亦师亦友,林长民留学日本时结识梁任公,1912年梁任公回国后,林长民追随其左右。徐志摩在1918年夏拜梁任公为师,当时林长民随团访问日本,不在国内,错失结交之机缘。在陈学勇、于葵编注的《林长民集》一书的插图中,尚存林长民自日本箱根寄林徽因的明信片,可以参证之。其二,梁启超是民初研究系的领袖,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其中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林长民、汪大燮、蹇季常等众多精英人物。蒋百里是徐志摩的亲戚长辈,徐在京读书时,曾寄宿在蒋家。张君劢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胞兄,这些关系都为林长民和徐志摩的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三,他们二人都曾在杭州、海宁学习生活,只是时间有先后。海宁是徐志摩的故乡,林父林孝恂曾做海宁知县,林长民亦曾随父学习起居。相同的生活环境为他们的交往增添了天然的纽带,书法家张宗祥是徐志摩的乡里长辈,亦是林长民的朋友。他在《论书绝句》中曾提到他十七岁时与林长民相识于海宁州署,即如今的盐官,据张宗祥生年推知当是1899年相识。
尽管林长民与徐志摩的交往非常密切,徐在留学归国之后起居的松坡图书馆(石虎胡同七号)与林宅并不远(林宅即雪池胡同双栝庐),很可能在1923年、1924年经常造访林府,但在现存史料中很难找到时人对二人交往的记录,只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北京的报纸曾经报道他们演出《齐德拉》的盛况,留下些许文字。比如1924年5月10日《晨报》第六版曾有一段文字:“林宗孟君须发半白,还有登台演剧的兴趣和勇气,真算难得。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第五幕爱神与春神谐谈,林、徐的滑稽神态,有独到处。”
虽然鲜有朋友谈到他们的忘年交,但从二人的书信、诗文中,或可管窥林、徐交游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