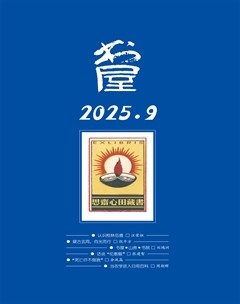一
古椿书屋,原址在沱江镇北门内的文星街文庙巷。幼年时,古椿书屋就给我一种与“新”相关的感觉。新知识、新气派、风琴和剪纸的林林总总,都融入了我喜好新奇的眼睛。
我进入初中的时候,学校设在文庙。学校要扩建,紧邻的古椿书屋就要搬迁,据说迁往南门外的白羊岭去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镇子里偶遇,有人建议去爬南华山,大家几乎没有异议地开始了这场体育活动。几个人一口气爬到山顶,原先的小庙早已荡然无存,所剩一点松树,七零八落。小镇就躺在脚下,远远一片灰色,顺带把每个城市都具有的喧嚣消解得似有若无。灰屋顶在小巷的断续分割下,密密麻麻,只有沱江自北而来,画出一笔漂亮的蓝色。或许是因为年轻人体力过剩,也可能是因为意犹未尽的不甘,有人提议不要从原路返回,而是开辟新路,从茅草刺窝林中直冲下去。这个勇敢的想法得到大家的赞同,等到把无数的芭茅荆棘、松树栗树、野蕨葛藤甩在身后,全身臭汗淋漓略有后悔的时候,都已是精疲力竭。不过,人家的院墙已是清晰可见,大家不约而同地止住了脚步。一阵清越的小提琴声自山下的人家传来,较有见识的朋友惊叹:是舒曼的《梦幻曲》!被优美的琴声所吸引,我们几个年轻的莽汉,冒昧地敲开了一家小院的大门,这竟然就是白羊岭的古椿书屋!
前几年,我在同当年拉小提琴的五满(五叔)黄永前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唏嘘不已。在那沉寂的环境中,这首优美的《梦幻曲》,真是一串难忘的音符。
让我沾到书卷的气息,还是真正进入古椿书屋后的事。我们两家原属世交,黄永玉先生后来告诉我,自我爷爷起,我们家就与他们家过从甚密。
1974年仲夏,我已经是在大山里面务农的知识青年了,接到消息赶回县城,见到永玉先生。先生趁着被批“黑画”的间隙,回了一趟凤凰。他见我风尘仆仆的样子,用钢笔在卡纸上为我画了张肖像,一边示范,一边告诉我:“慢写,也很重要!锻炼你的造型能力!”
几个画画的年轻人聚在他的身边,儒龙兄在城里混生活,还能请先生吃个饭,我和兰兄、马三只作陪。先生从不喝酒,但很高兴为我们每人作了个斗方。问我:“临帖吗?”“临哪家的?”听我回答说临唐楷,先生马上又说:“临魏碑试试看!”随即为我用四尺斗方写了一幅书法作品“宋·陈与义词”,并说:“临《张黑女墓志铭》,进去了容易出来!”之后,我从唐楷转入了临魏碑的学习,如《张猛龙碑》、“二爨”、《张黑女墓志铭》、《龙门二十品》……
关于批“黑画”,除了在报纸上公开的那些事,先生同我们也讲了一些当时难以了解的细节,但是结果会怎么样,他自己都难以预料。在车站送别时,我看见车窗里他举起一只青筋暴起的拳头:要坚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常有回乡的机会。有一回,在白羊岭古椿书屋,我把速写本拿出来向先生求教。先生看了以后问我:“你会画多少种树?”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算着,好半天才红着脸回答:“恐怕有十七八种树吧!”先生说这还很不够。又问:“分得清水成岩、火成岩吗?”这下我真的被考住了。先生告诫我,不仅要勤画画,还要长知识,要多读书,包括那些自然科学的书,比如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
后来,当我的木刻作品发表在《湖南画报》上时,想不到先生又问我:“创作时用不用速写作参考依据?”见我摇头,就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长期积累的形象,要装在这里!”他用手指着自己满头乱发的脑袋说。
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永玉先生在沱江边买了一座废弃的关门,改建成一座小楼,名为“夺翠楼”,小楼后是南华山的大片翠色。正应了《往日,故乡的情话》中的那句:“远处一大片绿中的小点,是南华山和我。”房子虽小,却充满诗意。
当时流行的做法是,人一旦有了点钱,就迫不及待地用白色瓷砖去改造古朴的木房子。他算是作个示范,这样建房,好看!幸好这个示范来得及时,古城得到应有的保护,才有了后来旅游经济的繁荣。这,可算是先生同故乡的一次对话,一次深情的对话!
新房建好后,尽管房间很窄,最窄处不到三米宽,他笑着作了一首《归乡赋词》,记得最后几句:“崖上蜗居,嗟来回旋,一笑窗开赏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