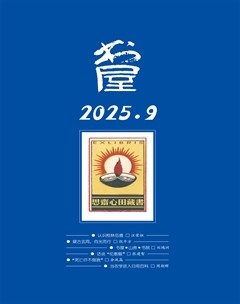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天色已晚,唐僧问悟空:“徒弟,今宵何处安身?”悟空回答道:“师父,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这段话悟空好似在点化唐僧,也预示着这一难要让唐僧明白,自己开始出发时,是个盼望温存的“在家人”,只是打着“出家人”的幌子上路,只有认清自己,才能继续前行。“在家人”是没有经过历练的人,可以温床暖被,没有风餐露宿的忧愁;“出家”即走出家门,不仅仅是皈依佛门,还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例如修行的意义。此时,唐僧的行动已经如悟空所说的出家人一般“戴月披星,餐风宿水,有路且行,无路方住”;然而唐僧的内心还有一丝“在家人”的意念。悟空所理解的“在家人”是无忧,“出家人”是随缘,“出家人”要抛却许多“在家人”的享受,这也是《西游记》所要表达的行脚僧与一般人的不同。悟空借此点化唐僧,不必羡慕别人,只要自己选好了一条路,那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行不多时,唐僧看见一条河,宽阔且深邃,八戒投下一颗鹅卵石沉入水底,悟空放眼望去,看不见边岸,以他的法力,寻常时能看三五百里。唐僧听到悟空说河水宽阔无边,声音哽咽地哭了。悟空引唐僧来看石碑,石碑上写着“通天河”,上有十个小字“径过八百里,亘古少行人”。唐僧看见,滴泪道:“徒弟呀,我当年别了长安,只说西天易走;哪知妖魔阻隔,山水迢遥!”西行路上有诸多艰难,唐僧所想的是困于路上,苦于妖魔阻隔,这何尝不是普通人的想法?唐僧弱化了圣僧的形象,变成了普通人。人们出发之前,百般盼望做一件事,对这件事的难度估计不足,一旦得知了此事的难度后,便难免忧郁。在西行路上,摆好“心”的想法,跟随“意”的脚步,该“感性”时就感性,该“理性”时就理性,这时的唐僧开始正视自己了,也是他进步的开始。书中多次提及悟空是“心猿”,白龙马是“意马”,悟空可以理解为西行人的“心”,白龙马寓意着取经人的“意”,八戒是“感性”的代表,沙僧是“理性”的代表,他们共同探索着取经道路。
在距离通天河不远处,有人家可供借宿,唐僧和徒弟们去了。在与老者的谈话中了解到,二位老者一个名叫陈澄,一个名唤陈清,与唐僧同姓氏,作者借此澄清唐僧取经的初衷,从而反思功利与非功利的区别。两位老者不断地行善求子,通过修桥补路、建寺立塔、布施斋僧,以求神灵赐福,终于老来得子得女,男孩叫陈关保,女孩叫一秤金。两个孩子的出生时间与唐僧从东土出发的时间差不多。作者要澄清的是,唐僧一开始取经的目的是“名”,他本以为自己西行是为了自我解脱、度东土人,现在才发现是为了忠于皇帝、为了自家名声。陈清、陈澄二兄弟做善事是为了求子,就信仰而言,他和二位老者一样,并不纯粹,他们的目的隐藏在所谓的“正”的信仰之中,不易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