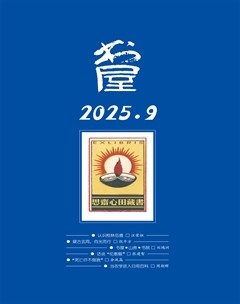父母去世后,我在整理旧书时找出不少学生时代的藏书,其中就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购读的《家庭日用大全》《花镜》《少年科技制作》等书。
1980年暑假,母亲参加在厦大举行的高考监考兼评卷工作,得了一笔名为“防暑降温补贴”的奖金,给了我五元钱买暑假课外书,我迫不及待到书店将惦记很久的《家庭日用大全》《花镜》等书买下。顺便提及,《家庭日用大全》标价一点四元,这在大学讲师月薪才七八十元的当时并非小数目。此书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城市生活日用指南,举凡日用品保养、洗涤保管衣服、裁剪、刺绣、编织毛衣、烹饪菜肴、打造家具、盆栽养鱼、病伤防治、美容养生至家庭琐事处理等,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此书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从出版印数可见一斑:1980年4月初版后,紧接着在7月就重印,印数一下就上了五十二万册,到当年9月就进行了第八次重印,印数达到八十五万册之多,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当之无愧的超级畅销书。遥想当年,国家拨乱反正、百废俱兴,这类书的热销似乎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2023年,我走访福建南平的“建本文化展览馆”,接触到大量明代建阳民间刻印的日用类图书,恍然想起家里尘封的《家庭日用大全》,找出翻读之下,感受到一种古老知识体系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的历史传承。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读物:日用类书之源流
日用类书是类书的一种。所谓类书,是对群书中的各种知识和各种资料进行分类汇编,以便翻阅检索与使用。类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即所谓“包罗万有”;二是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也就是“随类相从”。这两个特点很像近代西方兴起的百科全书。
我国早期的类书主要有三种:帝王御览、文人獭祭辞藻和士子应举指南。虽然“类书”一词直到欧阳修编撰《新唐书·艺文志》中才出现,但其起源却远早于此。曹魏时期曹丕敕撰的《皇览》是类书之祖。南北朝时期有《华林遍略》《科录》等多种类书问世。隋唐之际,官修类书风气颇为浓厚,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等,主要供文人词臣写作诗文参考。垂至两宋,随着文治时代的到来和图书刻印技术的发达,类书撰写和出版形成潮流。宋代官方修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类书规模宏富,囊括万有,文人士子无不受其泽惠。在官修类书的影响启迪之下,民间私撰类书之风兴起,出现了如《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古今源流至论》《玉海》等面向科举士子的类书。
南宋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农业生产达到历史高峰,带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同时,南宋政府大力兴学,文化教育相对普及,识字人口远超前代。各种社会需求互相激荡,广大民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费需求。于是,一种新型的类书在民间悄然出现并渐成潮流,这就是后世学者通称的日用类书。其中所载的内容不再是传统类书所包含的诗文典故、官场指南或科举应试攻略,更多的是涉及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诸如居家日用、游艺消闲、通俗文艺等,以满足世俗百姓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其代表作品有南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温革的《分门琐碎录》等。与以往那些面向皇室、官府或士大夫阶层的类书不同,这类日用类书开始关注城乡居民的需要,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识技术分门别类,汇编刊载,以便查询使用。到了元代,日用类书朝日常化、实用化趋势更为明显。元代中期出现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载内容涉及家居日用、官场应酬、市井营生、休闲娱乐和书房清玩之类,囊括民间居家日用所需的各种知识技术,如农桑、医药、饮食、穿戴、路途、气象、历法、赋税、刑律、算术、尺牍、风水、诉讼、劝善、礼法等。或采自典籍,或来自民俗俚语,或出于经验心得等。
从读者对象来看,宋元时代的日用类书基本上还以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主,如陈元靓的《事林广记》载有大量有关文房、词章、文籍的内容;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文房”“为学”“仕官”“为吏指南”,则明确了是以科举士子、世家子弟或各级政府衙门的官吏为主要读者对象,虽有涉及耕织、工商之类的日用内容,但比例很小。上述读者受众群体的狭窄,导致这类书籍的传播范围很小,仅限于在上层社会流传。到了明代中期,类书的读者面向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日用类书热:明代知识通俗化背后的思想哲学
明代是我国古代类书出版的黄金时代,而民间日用类书则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内容上看,明代日用类书可谓包罗万象。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出版研究》一书统计,目前在各类书目文献中能看到的明代日用类书,仅在万历年间以后出版的就超过两百种,如果加上那些散佚或没有被记录的,数量更为庞大,完整存留至今的亦有不少。2004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由酒井忠夫监修的《中国日用类书集成》十四卷,收入晚明出版的日用类书六种,其中大部分是明代建阳坊间的刻本。2011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十六卷,收录明代各种书坊刊刻的日用类书四十四种,是目前明代日用类书集刊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