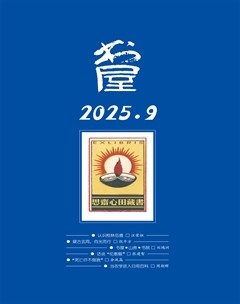读大二那一年,在春夏之交的时节,埋头埋脑做作业和应付考试之际,没有谈恋爱,却写了一篇关于爱情小说的评论,题为《看〈星星·月亮·太阳〉》,在《盘古》杂志发表,洋洋六千五百字。作者徐速把一男三女的爱情写得“崇高无邪”,我幻觉自己是个文学批评家,东征西引一些文学作品做比较,对小说的内容和技巧加以评论,褒贬都有。徐速先生器量大,把拙作转载于其主编的《当代文艺》。应付考试期间,为什么还费时费力写这篇长文章,用纸上谈兵的恋爱观来看《星星·月亮·太阳》,堂皇的理由是:“当时我有感于香港的文学,是好是坏,都甚少得到注意和评论,于是毅然写作本文。”
1969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76年回港,在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经常参与本港的文学文化活动,而关注本土是当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理念。几年后,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一大议题:香港的过去有什么文化表现,未来的岁月又会如何?内地的学者对香港也十分关心,十分有兴趣研究:这个即将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生长出落得什么样子,“香港学”由此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发表为数可观的文章,对香港文学的本质和现象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从而有1985年春夏之间《香港文学初探》(以下简称《初探》)的出版。
《初探》是首部论述香港文学的专著,引起港内港外很多人注目,好评甚多,也有表示不满的。1987年,北京的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内地版,内容与港版全同;1988年,港版第二次印刷。论者对我主张的“多论作品,少贴标签”,对我的“正视通俗文学的态度”,对我将香港作家分为四大类别,对我通过本书“彻底否定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对我“灵活”“精彩”的、宏观微观兼备的析评手法,予以肯定和鼓励。2005年,内地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香港文学的王剑丛教授这样回忆:“1986年我托友人从香港买了黄维樑博士的《香港文学初探》,翻开来一看,我如获至宝”,此书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香港文学的基本状貌”,“对一个开始香港文学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它就像一幅指路图,也是一本入门书,我是放在身边随时翻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