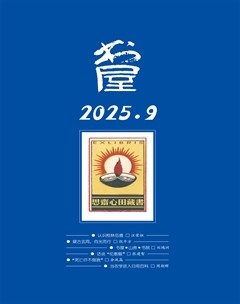十年时光弹指一挥,日历翻到了2025年1月。回顾十年前,我正在一章一节、缓多速少地撰写《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以下简称《走出乡土》),并于6月1日草就了后记初稿,整本书稿初步完成。虽然该书正式出版是在2017年4月,但从完成初稿算起,于今已近十年光景。在这近十个年头里,这本书引起的反应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乡土中国》这本书,同时通过人们对《走出乡土》的称誉和批评,更深层地思考和理解了当下的社会进程。在《走出乡土》修订版出版之际,我想把其中的一些要点写下来提供给关心拙著和乡土中国社会变迁的读者,以作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次交流研讨,共同探索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走出乡土的历史进程。
2017年《走出乡土》出版时,我还未曾闻得一丝消息,《乡土中国》即将入选全国高中生一年级语文课的整本书阅读书目。次年冬季,我在厦门参加第五届“教育阅读节”高峰论坛期间,受邹春盛老师之邀在厦门外国语学校给高中学生作了一次关于阅读《乡土中国》的讲座,才知道部分地方的高中生已试点整本书阅读。2019年,全国高中生开始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那么,《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与我有何渊源?就是无意间,拙著《走出乡土》成了中学语文教师和学生阅读《乡土中国》的辅助教材。这是我写作《走出乡土》时未曾预料到的。而之所以成为辅助读物,正在于师生们几乎一致反映,《乡土中国》阅读起来比较困难,而通过阅读《走出乡土》读懂了《乡土中国》。
这个事情使我感到惊讶,惊讶的是从未想到过“真佛只说家常话”的费孝通先生以令人触电般惊艳的文字和散文笔法写就的《乡土中国》,竟然遇到众多读者读不懂的问题。第一次听到年轻学子反映读不懂《乡土中国》是《走出乡土》刚出版不久,《新京报》记者兼编辑罗东联系我想做个关于《走出乡土》的采访,他向我提到这个问题,之后便不断听到这样的反馈。2019年秋季,我为北京朝阳区高中语文教师专门讲了一次阅读《乡土中国》,讲座之前进行了一个小调查,发现百分之八十五的高中语文教师在阅读《乡土中国》中遇到不同类型的困难。在高中生中,这个比例更高,困难更大。感觉困难的主要原因,总结起来有三:一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文字过于“文言”,不是这个时代的通行语言,因而难以理解;二是书中的学术术语和人名;三是我国走出乡土的步伐太快,新生代缺乏乡土社会的生活经验。第三个原因比较容易理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让当下的年轻人生活体验的多是工业化和城镇生活,而非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生活经历。第二个原因也还好理解,学术术语没遭遇过,众多术语初次接触一下子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什么“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等,在社会学思想家方面,什么涂尔干和滕尼斯,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弄不明白,缺乏专业背景知识,阅读起来确实会有些难度,这都很可以理解。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费孝通的语言也成了问题,看不懂,甚至因为看不懂而认为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