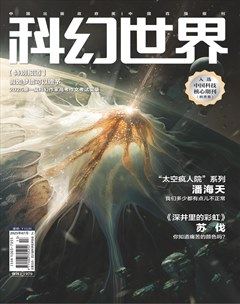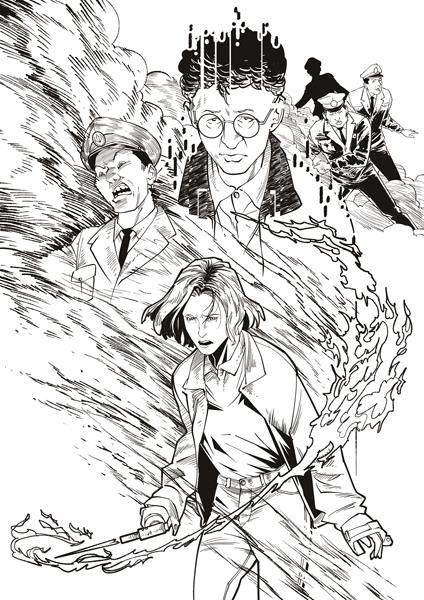
1
“你见过痛苦的颜色吗?”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深井”里作业时听到这个问题,甚至运气好或者说不好的时候,一天能听到十几次。通常我会回答说是“黑色的”或是“白色的”,不是因为我真的这么认为,而是根据经验这两个答案最容易得到认同,也能更快换得耳根清净。
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用白色和黑色形容痛苦的人是最多的。也许是因为黑色隐喻着压力,而白色像是抓不住的虚无。我也不是没有经历过绝望,没有见到过痛苦。但我不觉得那是黑色或是白色的,在那个时候我痛苦得看不到任何颜色。
但今天我不打算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你觉得是什么颜色的?”
我一时没有听到回答,也许是她陷入了沉思,也许她只是想问我,自己并不想回答什么。于是我专心做自己的事,继续扫描她的大脑,基底核的多巴胺水平比上次还低。但还好,只是腹侧被盖区的数值低,黑质是正常水平,也就是说她虽然有情绪问题,但至少还没有患上帕金森的风险。
“您不用担心,您只是有一些情绪问题,目前没有对生理产生影响的征兆。”我宽慰她,开始生成诊断报告和治疗方案。
诊断报告是自动生成的,并不需要我做什么,患者的基础信息和检查数据没有更改的余地。我看着文字与数据在她的姓名下飞快地显现出来,用最大的字号,闪着浮夸的金色的光。
光的颜色患者看不到,是仅疏导师可见的。这浮夸的金色是我自己调的,在黑暗一片的“深井”中金色显得尤为好看。
大脑是如此庞杂的一个系统,意识、记忆、情绪……而“深井”系统能触碰到的,仅仅是情绪的流动与旋涡。那就像是一口无尽的深井,向上飞不出,向下也探不到底。
脑中虽然有电信号,但完全不是能被看到的那种,畅游在其中的我本来只会看到一片黑暗,看不到电信号的迅速传播,更看不到神经递质的缓慢扩散。但人类总是能把不可见转化为可见,无论是不可见光、电信号还是化学物质。此时我正看着黑质里产生的多巴胺向着纹状体流动,而另一股多巴胺则从腹侧被盖区流向前额质皮层……我将这两股多巴胺分别染成深黄和浅黄,加上了点点荧光,就像是流淌在黑暗中的沙,掺杂着钻石或是玻璃。
为了看得更清楚,疏导师可以按自己的习惯更改颜色。想把黑夜一般的背景改成明亮的白色也可以,毕竟这颜色只有自己看得到,患者只是躺在床上,无论睁眼闭眼,都看不到自己脑中的情况。
但我从来没有改过黑色的背景,虽然明亮的颜色会让人的情绪更愉悦,多少对冲掉一点儿疏导时带来的抑塞。来疏导中心的患者,都是有严重情绪问题的,或抑郁或暴躁或麻木……情绪从来都会感染人,整日在毫无正向情绪的环境里,满目的黑色只会让情绪更加低沉,更容易向着被他们同化的方向滑落。
但对我来说没有关系,情绪是我最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AI的帮助下,诊断报告飞速生成了。治疗方案本也可以通过AI生成,但我从来没有用过,一直自己写。我坚信我比AI总是要强那么一点儿的,否则何苦非要我来做这事,直接用AI不就好了,那就不会有任何支出、成本和代价。
“沈雨,”我念着诊断书,和患者确认治疗方案,“和你确认一下诊断方案。虽然你已经在疏导中心接受过多次情绪疏导,但你也看到了诊断书,你的抑郁倾向依旧没有好转……”我忍住了“反倒更加严重”这样的话,诊断报告上写的都有,倒也不需要我每一个意思都表达出来。
沈雨打断我,“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我知道流程的,把诊断书给我签字吧。”
我把视野切到疏导室的监控,老板真的是够抠门,甚至舍不得装专门的高清电子眼,说监控的视角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多一份重复的设备。老板这么说,我就这么认了,他是老板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就算我告诉他这种俯视全屋的视角太高太广,观察不到患者的微表情,老板也只会反问我都能进入人家的脑子了,干吗还要从表情来判断情绪?
所以我只能什么也不说,我那点小心思藏在我自己心里就行了。我透过监控看着沈雨,看着她的眉她的眼,抿成一条线的嘴唇和微微泛白的脸……我当然能看到多巴胺、内啡肽、5-羟色胺等这些神经递质在她脑子里流淌的样子,但我更想仔细看看她的脸,看看她的一颦和一笑。
虽然很久都没看到过她的笑了。她来疏导中心从来没有笑过。
我调用了一只机械臂。说是机械臂,只是一根长长的可折叠的机械杆,可活动的一端安着数据板,上面显示着沈雨的诊断书。诊断都是在患者清醒情况下进行的,因为睡眠时人脑活跃程度会下降,但大部分患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也许是为了缓解疏导室中仅有自己的紧张与不安。但沈雨一直都是睁着眼的,她就一直盯着白色的天花板,在监控不高的清晰度下,我看不出那眼里盛着的是什么眼神。
机械臂带着数据板移动到她面前,刚好遮挡住她的眼睛,但她在数据板上端轻轻压了压,特地露出了眼睛。我这才意识到,她不是一直盯着天花板看,而是盯着监控,她知道我在用监控看她,她一直在盯着我的“眼睛”。
她把拇指按在数据板上,确认了诊断书的全部信息。这个过程中她一个字也没看,眼睛还是只盯着摄像头,眼神一瞬都不瞬。
我熟悉她这个样子。当她执着地想要什么答案的时候,她就会这样盯着对方的眼睛,视线连一瞬都不移开。
“你见过痛苦的颜色吗?”她又问了一遍。
显然,这不是一句闲聊。她在很正式地问我这个问题,并且执着地想得到答案。
我想反问她,我有没有见过痛苦的颜色,她难道不知道吗?我痛苦的时候什么样,她难道没见过吗?
专门跑到我这里来明知故问,又有什么意思?
如果是之前的我,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呛声了吧。但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因为情绪上头,于是我只是客观地提醒她:“我们的对话都是会被监控并且记录的。”
“所以呢?”她反问我,语调中带着一种细微的、只有我能听出来的挑衅。
或者该称作是“找事”。
但此时的我只是平静地说:“谈论私人话题是被禁止的。如果我违规,可能会被开除。”严格来讲只是禁止疏导师谈论自己的私人话题,并不禁止患者的。患者当然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疏导中心是鼓励他们倾诉的,因为可以缓解情绪问题。
沈雨当然也知道这点,但她没有揪着再呛回来,反倒是闭上了眼,抬起一只手遮住了眼睛,也遮住了缓缓淌下的泪。
因为监控不够清楚,我没有看到她眼角的泪。但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我能听出她什么时候在装哭,也能听出她什么时候装作自己没哭。
“如果是之前,你现在已经和我吵起来了。”
我不再说什么了,沉默地按治疗方案释放神经递质。很快她的情绪将得到安抚,想哭的感受降低……不管她现在是因为什么引发的情绪问题,很快都将不再重要。我还违规调高了5-羟色胺的释放,让它们像沙砾一般堆积,压在“睡意”的天平上。
5-羟色胺并不是安眠药,不能强迫一个坚持不肯睡的人去睡觉。她努力睁大眼睛驱赶睡意,抓住最后的清醒说:“你说过的,你说痛苦是彩虹色的。你不记得了吗?”
我当然记得,那是我在婚礼上的誓词。我那时候和所有傻子新郎一样,以为未来必然是光辉而明亮的,自以为幽默地开玩笑说:“很多人不知道,痛苦其实是彩虹一般的颜色。”
这句话取得了我想要的效果,婚礼上一片冷场,当然除了新娘。我对她信任的目光报以微笑,继续说:“希望我们未来遇到痛苦的机会,就跟亲眼看到彩虹的机会一样小。”
我后悔了,我当初就应该说那句最普通的:“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这样我就能对沈雨说别再来找我了,死亡已经把我们分开了。
2
把痛苦称作彩虹的颜色倒不是我在婚礼上的心血来潮,而是我很久以来的思考。那时候我在做抗抑郁研究,传统的抑郁症疗法是药物疗法,但药物治疗治标不治本。无论通过消化道吸收还是直接静脉注射,药物只能进入血液,但因为血脑屏障的存在,无法进入脑组织。
于是,我干脆在人的脑壳上钻了个洞。
说起来挺吓人,其实只是普通的一个微创手术,创口甚至只有针孔大。纳米粒从这针孔大的创口中注入,游至血脑屏障的基底膜附着其上,纳米粒的网将整个大脑网在其中。这个“网”是真正意义上的网,每颗纳米粒都伸出一根长长的尾巴,归束在颅骨的创口处,通过残留的纳米粒与外部设备用无线网络连接。
这张纳米网,便是深井系统。
深井系统比我最初设计的应用场景更广阔,不只是用在抗抑郁治疗上。深井系统的运作方式,是利用纳米粒中搭载的碳氢氧氮等元素合成出神经递质,直接作用在脑内。我称这些合成原料为递原。纳米粒就那么点,装载的递原自然是有限的,但起码也足够三五年的消耗,消耗完再补充便可。
直接在脑部调节神经递质,当然不只是抗抑郁,更能调节人类的所有情绪,甚至能疏导睡眠、提高注意力……无论哪一项都前景可观。
即使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动物数据,人体实验的申请还是迟迟拿不到审批,难度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医学和药理学实验。那时候我还是个傻了吧唧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拿到审批是迟早的事,毕竟我的动物数据如此完美,唯一的问题只是再等下去我就真没钱了。
不只是我个人没饭吃的那种没钱,虽然这种也已经很惨了。但比没饭吃更惨的,是研究没钱了。我吃饭可以省,但我的投资人不能等。再不进入下个阶段,就要么撤资,要么让我滚蛋。
于是在傻了吧唧和乐观主义的共同作用下,我决定私下先做实验。我先把深井系统给自己脑壳里整了一套,虽然我没啥情绪问题需要调节,但可以借此调节去甲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让我的决断更理智、记忆力更强大。
最常见的神经递质是七种,即多巴胺、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谷氨酸、γ-氨基丁酸和内啡肽。我用七色光为它们赋予颜色,这样我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在脑中的多寡。就像是一张用情绪涂抹的画。
“照你这么说,影响人情绪的就是七个葫芦娃?”
这是沈雨当年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她是来应征做我的志愿者的。因为研究经费捉襟见肘,我也给不出什么报酬,只能希望这世上有好奇心足够旺盛的人。沈雨是第一个来应征的,也是那天唯一的一个。我特地向她讲了整整一天的研究原理,既狠狠满足了自己的倾诉欲,又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感。
讲完我觉得自己一整天都不需要任何神经递质调节了,整个人舒爽极了。
那时候的沈雨看上去也是乐观而阳光的,她好奇地问我:“你刚说,有的神经递质会让人兴奋,有的会让人满足……如果在深井系统里同时释放这七个葫芦娃呢?人会怎样呢?会死吗?”
在药理学上,不谈剂量就谈效果都是耍流氓。神经递质并不只作用于脑部,不只影响情绪,甚至也会影响人的食欲、睡眠和心跳。但如果抛开这些生理层面的影响只谈对情绪的影响,倒应该不会致命。
就算抑郁症有自杀的,那也是人主动选择了死亡,不是神经递质直接导致的死亡。
“大概,会非常痛苦吧?”我回答她。
“所以说,痛苦其实是彩虹一般的颜色咯?”
3
和之前每一次一样,沈雨没在我这里问到任何她想要的答案。我操纵着纳米网释放神经递质,她的眼神逐渐空虚麻木起来。她会记得她来的目的,也会记得她一次又一次前来的执着,但她同时也会觉得这些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她心里装着的所有事,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让她痛苦的事情也是,让她执着不肯放手的也是。
甚至连我的离开她都没有注意到,她只是平静而麻木地躺着,全没发现有人刚刚退出了她的脑子。
沈雨是我今天的最后一个患者,退出来之后我一时无处可去。自从我死了,我就不需要住的地方了。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死亡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不需要还房贷也不需要交房租了。我的意识被数字化,成为网络上或是硬盘里的一串字节,我的思维和记忆全都保留了下来,除了情绪。
数字世界当然没有化学物质,缺乏神经递质的影响,我感觉自己就像AI一般冷酷而平静。
谁都无法带给我什么波动,无论是我死前的妻子,还是老板。
就算是老板威胁要开除我也不会。但若没有这个地方收留,我就会再没有去处,我会被关掉甚至是清除——在肉体死亡之后,真正意义上再死亡一次。
我虽然没有情绪,但我还有脑子。无论是出于理智还是逻辑我都不想死,于是我问老板,他对我的工作哪里不满意,希望我怎么改进?
老板没有直接回答,反倒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沈雨来的次数太多了?”
我不想和他打哑谜,径直问:“您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我本来还想添一句,“咱有啥就说啥,藏着掖着没必要。”临脱口时忍住了。倒不是我怕惹他生气,只是单纯觉得没有必要。我和他的沟通讲究有一说一,简单高效。多说一句话,都是对效率的拖累。
“你这样回答,我可以判定为生气吗?”他也直接问。
“你明知道,我现在没有‘生气’这个功能。”我回应道。
“我刚刚说的‘生气’可以仅是一种形容,并非情绪意义上的‘生气’。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对你抵触性反应的一种归类。”
“你可以在你的数据收集里,把这个归类为‘提升效率’或者‘节省时间’。”
“懂了。”他说,“归类进‘逃避’。”
沈雨本来是没有将我数字化的意愿的。我死后,我的一切由沈雨继承。我的一切对沈雨毫无价值,本该和我的骨灰以及我脑子里火化都没烧掉的深井网络一起埋葬。但有律师忽然找上了她,有公司想买下我的一切遗产,无论是研究、数据还是我本人。
死亡并没有带给我解脱。等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变成了数字生命。另一个数字生命自称是我的老板,他正在研究怎样让数字生命获得情感。老板刚说出他的研究方向,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买我和我的研究了。我告诉他没用的,我确实能轻易调整人类情绪,能让高兴的人忽然低落,也能让低落的人莫名兴奋,但深井系统没法作用在数字生命上,因为神经递质在这个赛博世界里是无法模拟的。
老板承认我说得没错,他的研究计划与此无关。他利用我的研究开设了这家疏导中心,通过深井系统对情绪的调节来收集数据,试图在其中找到情绪甚至是情感的规律,毕竟情感也可以说是情绪的叠加。
很讽刺,人活着的时候,一些人是老板而另一些人是打工人,没想到死了之后也一样。理论上来讲,我死后不再拥有财产和权利,老板应该也一样,无论是钱、财产、公司还是知识产权。但人类的特质就是总有办法钻空子,这个空子还特别好钻,甚至都不用想新主意,找个人代持公司就是了,曾经那些自己不方便或是不愿意做法人的老板就是这么干的。无论给钱还是欺骗,总能找到愿意干的人。就这样,老板不但能委托律师买下我的遗产,还能用公司开了这间疏导中心。
死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失去了辞职和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这家疏导中心,从公司到工作到老板,全都是我找工作时要远远避雷的。但我没有发言权,因为签合同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没有说“不”的权利了。这个事在法律上非常混乱,沈雨能卖我是因为她是我妻子,但因为我死了,这笔钱归她个人所有,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除非她还钱,否则我要给老板打一辈子工。鉴于我已经数字化了,这个一辈子可能比我想象的久得多。
我也不知道她想不想还钱,我没和她讨论过这个。不过我确实也没想让她还钱,一来我希望我死后她能过好一点儿,二来如果我失去了这份工作,服务器也就没有储存我这一小团数字代码的必要了,我便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虽然我活着的时候很想死,但真死了之后反倒不想了。那种痛苦和对解脱的渴求全都随着死亡消失了。并不是因为死亡已经让我达成所愿了,而是此时的我已经只是一团数字,没有大脑,没有多巴胺、内啡肽、去甲肾上腺素……我没有办法再痛苦起来了,我的情绪在这个数字世界里无处安放。
这样奇特的身份体验,让我在继续研究时有了新的思路。之前我一直以为,情感只是情绪的叠加,虽然不是简单地叠加,但没有情绪就不会有情感。但此时的我已经不具有任何的情绪,还是觉得自己似乎拥有若有若无的情感。
对于数据来讲,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单从数据来讲,我确实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但每次在疏导中心又一次看到沈雨作为患者出现时,我都会希望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了。
这种“希望”我无处归类,只能若有若无地归类为“情感”。
只有存在情绪问题的人,才会到疏导中心接受治疗。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能证明神经递质的调节是否会像药物一般成瘾,甚至是比药物带来更多的后遗症。只有诊断后被评定为不再适用其他手段干预的患者,才会在深井中直接接受神经递质调节。
沈雨会反复出现在这里,只能证明她现在的情绪问题非常严重。每一次她的诊断数据都更糟糕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现在活得如此痛苦。明明我已经死了,她摆脱掉所有痛苦的来源了,为什么她反倒过得更糟糕了?
“其实我也对这个问题很好奇,”我的老板说,“于是我去调查了她的现状。”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但我确实很想知道沈雨的情况。我的权限被锁在了疏导中心,我只能做疏导工作和继续情绪研究,不被允许登录外部网络,完全没有办法和她联络。
“她现在过得很糟糕。我买下你的钱她已经花完了,全都用来还债了。她还要一个人还你们的房贷,压力很大,几乎称得上贫困了。工作也很糟糕,做最恶心的事,加最长的班,拿最少的钱。她的工资完全没法覆盖房贷,她还要在加班的时间里挤出时间打零工,压缩日常消费……即使如此,每月还要靠各种借贷才能还上房贷。”
“我不明白。”我一时间只能说出这句话。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明明可以卖了你们的房子,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经济压力。虽然大城市的租金压力也很大,但她也可以带着卖房子的钱回老家,也能有不错的生活。”
不,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不明白。”
老板又懂了,“我明白,我明白。她也可以辞职不做这份工作的。她老板知道你们的事,因为你也知道,她有段时间没法去上班。老板就一直在用那件事打压她,说除了他没人会雇她了,除了低端岗位。我猜你知道生活艰难挣扎、事业毫无希望是什么感觉。”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想闭眼,但现在的我没有眼皮。我把这个“想闭眼”的冲动记录下来,纳入“我是否还拥有感情”的研究数据。
“当然,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问题,她明明可以离开这座城市。她的老板可以在这里散布她的过去,但触角总伸不到全国。”老板调用数据模型开始分析,沈雨的各种选择与出路延伸出来,辞职、卖房、返乡……无论哪一个,显然都比现在要好。
甚至哪怕她不离开这座城市,坚持辞职,也不像她老板所说的“找不到其他工作”。
“你要我做什么,才能把这个预测模型给她看?”他显然是来谈条件的,否则干吗要给我看这个?
“你误会了,我已经给她看过了,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调出监控来给我看,沈雨只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模型,就推开了数据板。
我很确定那一眼足够她看清屏幕上的内容,老板甚至做了闪光特效,布灵布灵地闪烁着“你的新生活”。
“真可惜,那个模型可是很贵的。”老板假模假样地感叹。
正常来讲,一个生活困苦的人,在得知有一丁点儿希望改变的时候,总会多看两眼吧?就像溺水之人看到稻草总会忍不住去抓。但沈雨拒绝得如此干脆,在清晰度不够高的监控下,我也能看到她眼里的决然。
她根本不想改变现状。
她的痛苦、她的抑郁,都是她故意为之。
“为什么?”就算她还陷在那件事里,总不至于用这种方法惩罚自己吧?
老板轻飘飘地说:“你想不到吗?这是她唯一见到你的方式啊。”
原来,都是因为我吗?
因为我被困在了疏导中心,她想见我只能来这里。但只有情绪问题足够严重才能进疏导中心治疗……
她不是没法摆脱现在的困境,她在故意折磨自己。她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全是为了来见我!
如果我还活着,此时已经被排山倒海的情绪压垮了。我本该在情绪的海洋里溺亡,但无论我的理智怎么告诉我这时候我该发疯发癫痛不欲生……我的情感,我的情感表示它不知道自己还存不存在。
“我不明白……”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如果我死后她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她为什么,为什么还要……”
她为什么还要杀了我?
4
我曾经在开玩笑的时候说过,痛苦是彩虹般的颜色。但真正的痛苦将我淹没的时候,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颜色。
痛苦其实没有颜色,它就像水一样,将人淹没。挣扎和呼救都没有意义,这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海。只有无望的窒息,无处可逃。
我和沈雨结婚之后买了房、买了车,就像所有的普通家庭。当然,我们欠了房贷和车贷,在这样的一座大城市,能够兼顾学区和舒适性的房子自然价值不菲,房贷当然也是。
但是没关系,我和沈雨两个人的工资养得起。
我以为我的研究迟早能拿到审批。正常来讲,审批就是走个手续的事情,当然有快有慢,但迟早都能拿到。我私下开启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招募了志愿者开始人体实验,只待审批手续完成,数据就能直接使用。
我那时候以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能保证我的实验绝对安全,我都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了,还能不安全吗?但没想到,实验还真的出事了。
一个参加实验的志愿者自杀了。
而且,就是从我的实验室跳出去的。
因为是在我的实验室出的事,我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和赔偿。财务困境的海啸扑面而来,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网络暴力具象化地向我围攻而来,骂我用抑郁症患者做研究,这个群体本来就容易有轻生的念头,全是我的研究加重了患者的症状,我就是那个丧尽天良的杀人犯。
我拼命在网上解释,自杀的人不但没有抑郁症,甚至比这些在网络上骂我的人都要自信和乐观。为了稳妥,我招募的志愿者都是没有任何抑郁倾向的。毕竟只是第一阶段的实验,而且我也没拿到审批,直接拿病人研究我也怕出事。在这个阶段,我只研究深井系统对神经递质的调节效果,针对普通健康的人群就足够了。
但解释没有用,人从来只相信更加易于传播的内容。很快他们扒出了跳楼的是一个基金经理,又开始说基金经理本来就是抑郁症高发人群,我要是连这点都不知道,我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诈骗;我要是知道还用他做研究,那就是明知故犯蓄意杀人。
经典的互联网诡辩。提出的人会自鸣得意,还会被一群人追捧说他是逻辑之神。
问题在于,跳楼的这个人,他真没有一点儿抑郁。这个人的自信乐观就差写在脸上了,就是那种觉得全天下只有他最聪明的基金经理,开口闭口都是你听不懂的词和这辈子见不到的钱,明摆着地炫耀自己的收入和业绩,字里行间横竖写着“我这种精英人士和你们不是一个圈层”。
瞧瞧,人家用词多专业,不但表示了我们不是一个阶层,即使我们认识了也不是一个圈子。
他来做志愿者,当然不是因为好奇或是想为研究做什么贡献。他听说有药物可以提升人的记忆力和专注力,也就是常说的“聪明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