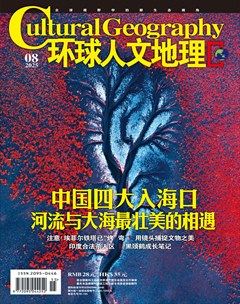二十多年前,大慈寺南门是一个菜市场和一片老房子,每天我都会经过那里送儿子上幼儿园,对那一带非常熟悉。但在2003年左右,幼儿园突然说要拆了,原因是要重修大慈寺,幼儿园正好在拆除的范围内。儿子只好转学,幼儿园连同菜市场和老房子很快就拆掉了,成了一片空地。
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突然就变得陌生了,准确说是把一个喝茶的地方弄没了。曾经在不短的时间中,大慈寺就是个大茶园子,庙不过是个空名,因为没有菩萨可供。用作“喝茶”的大慈寺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二三十年,慢悠悠的喝茶时光把历史沉到了碗底,而滚热的茶水熨烫着百姓的日常生活。那时候,作为“寺庙”的大慈寺却仅仅是一个名字,望着庙宇的檐角,只有在落叶飘下的瞬间才会感受到一点什么。
从唐玄宗敕建“大圣慈寺”开始,大慈寺的香火曾经盛极一时,这个寺庙堪称西南第一大庙。它有多大呢?最大的时候据说僧众上万,南边已经到了镗钯街一带,那曾是为武僧们打镗钯的地方,离现在的地方隔了好几条街。但后来慢慢缩小了,加上城市道路的分割,被挤压到了一个方块内,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缩到了一碗茶里。那时候,大慈寺的花茶五元钱一碗,从早可以喝到天黑。若是早上就去喝茶,中午还有面食炒饭供应,点碗杂酱面,面上盖一层臊子,小葱、辣椒,红红绿绿。接下来的半天时间也好打发,只消一张报纸,半盒烟。
大慈寺身处闹市中心,与尘嚣近在咫尺,却独得一片和静,这是很难得的。二十多年前,那是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做副刊编辑,上午去处理稿件,下午基本没有什么事情,就到大慈寺喝茶。其实,那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等于是把办公桌挪到了大慈寺,见见朋友,也顺带约约稿。多数时候,我每周有两三个版的稿子就是从大慈寺里约到的,当时我编的副刊名叫“望江”,主要发诗歌、散文,里面的不少作者是大慈寺的常客,都是些博学多才、口齿伶俐的家伙,喝茶也不忘在腋下夹着本卡夫卡或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