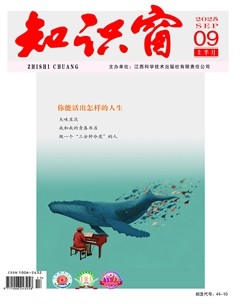我曾经有个习惯。
每次不知道吃什么时,我就打开外卖历史订单,找个排名靠前的点“再来一单”。通常,牛羊肉米线、绵阳米粉、肥肠粉、过桥米线……同一品类下的不同组合,都是我的首选。
焕宇对此总是很无奈地说:“你这不是吃饭,是在用碳水顶饿。” 虽然她也羡慕我能在“碳水炸弹”的常年包围下依然不发胖。她则和我截然相反,对美食怀揣着朝圣者般的热忱,每到一个新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搜罗当地“必吃榜”,献上虔诚的一筷。
想想,我们对美食的执着,原本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智慧。在远古岁月里,人类祖先需要在荒野中匍匐求生。今日挖到几株苦根茎,明日捡到两颗甜浆果,偶尔蹭到猛兽啃剩下的残骨,便是饱腹的恩赐。正是这种对食物多元化的渴望,推动人类驾驭火种、驯化谷物、精研烹饪,最终使人类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
而我,却像在逆向进化。我也看美食Vlog(视频日志),听主播的牙齿与食物摩擦时发出的咔咔声,画面有趣又治愈。但说到吃一口,我的兴趣立刻缩回安全区。琳琅满目的美食,我连尝试的想法都没有。
心理学认为,早期缺失的某一部分情感,会让人在成年后过度补偿。但对食物,科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童年时期单调的饮食结构或营养结构,会重塑大脑的味觉编码。
很明显,我是后者。小时候,家里饭桌上永远是几种固定搭配:青椒、土豆、豆腐、五花肉、泡菜。祖母做饭讲究“管饱就行”,葱、姜、蒜等配料很少同时出场。她有句名言:“菜嘛,就是搭筷子的。”
在这反向驯化下,后来的我仿佛也成了个年轻的老太太。记得第一次吃山竹时,我心想,这么寡淡的水果凭什么卖那么贵?榴梿,光是臭味就已经让我退避三舍;张牙舞爪的红油小龙虾,看一眼就犯晕。去海岛城市旅行时更是夸张——面对满街的海鲜,我饿了几天,最后去超市买了几桶泡面。
从前,我会用长情来美化这明显的心理缺陷——我能十年如一日地吃同一种食物,多专一。
但我也慢慢意识到,我的味蕾早被匮乏驯化,把单调的味道标记为安全信号,继而本能地排斥新食物。挑食的背后,藏着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因素。
这种固化并非无解。这两年,在焕宇的陪伴与引导下,我开始有了“逃离可以,但没必要”的潜意识循环。2023年春天,她给我蒸了一锅小龙虾,保留着水产品甜腥的原味,配上简单的酱汁,于是我吃了人生第一只小龙虾,吃得小心翼翼。一年以后,她笑着聊起此事,说道:“你这一年吃的小龙虾,比过去十年还多。”
改变,始于接纳。一个人若没见过太阳,的确能在黑暗里自欺。可一旦见过了光,味蕾和心智都会苏醒。现在的我,也会主动点上一块熔岩巧克力,能分辨三文鱼不同部位的口感。
对美食的探索,本质上是对世界的情绪感知。人间烟火气,需要不同的味道作为引线去点燃:辣是热烈,甜是治愈,苦是沉淀。允许自己体验多元的食物组合,其实也是在规训大脑:在安全区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味蕾风光。
这种觉醒不止于饮食。从前我对打游戏、社交、探索新文化都缺乏兴致,但如今我都愿意去尝试了。低欲望的背后,是心理与生理的双重禁锢。而打破它,或许就是从吃一道从未见过的菜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