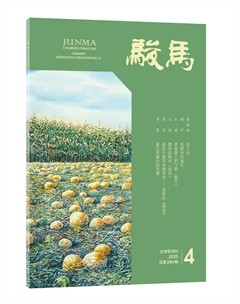一
十里铺的一户小小篱落里,兰花正开得清妙。
篱角那淡黄色的花朵,半舒着鲛绡似的瓣,楚楚的,有着摄人心魄的灵气与清香。而一片片狭长的墨绿色的叶子,却透着不可侵犯的尊贵。
小姨娘倚着廊柱,看兰花,晒暖阳,嗑瓜子,闲闲淡淡的。
几只灰羽白翅尖的鸟,蹦蹦跳跳地在地上啄食瓜子皮。小巧的鸟爪子,紫红紫红的,像开在地上的两朵纤巧花瓣。
“娘,快看,哪来的野鸟?小模样真俊。”
姥姥撩开绣满蓝花的门帘儿,像撩开一朵鸢尾花。探头,望天。天蓝汪得像绸缎,一铺千万里。几缕纤长白云,宛如几瓣白菊花,绣在蓝缎面上。
“今儿天这么好,晚上能唱戏了吧?”姥姥自言自语。
镇子上驻了兵,戏园子关了门。一出《穆桂英挂帅》刚唱到“接帅印辕门点兵”,就停了。从杏花满枝,到青杏累累,一停就是月余。小姨娘在篱笆院天天吊嗓子,练功。说,再不唱,人都锈了。
小姨娘是戏班子的角儿,镇子上“梨香园”的台柱子。闺名春兰,艺名小苍兰。青春貌美,头发丝都是戏。戏台上一抬手一扬眉,都藏了万种风情。天生丽质难自弃,那才叫一个惊艳。
“梨香园”关门,小姨娘回了乡下。没有戏唱,急得嗓子眼伸手。
可仗都打到十里外的码头集了,每天都能听到零零散散放鞭炮似的枪声。人心惶惶,谁还有那份听戏的闲心?
二
从集镇上跑回来的二姥爷,面带惧色。“小小的码头镇,驻满了兵。黄军服,钢盔,呜哩哇啦,蚂蟥似的。镇子上的人几乎都跑空了。没跑出去的,门栓顶得死死的,小羊羔儿,小狗崽儿,都拿布条缠住嘴。吃奶的娃娃都不让哭,一哭就拿奶头塞住嘴。昔日人欢马叫的镇子,眼下那叫一个死静死静的,生怕蚊子放个屁,把日本兵招来了。”
小姨娘听二姥爷说完,不怕,反而咯咯笑。“二叔,您的裁缝店关门,家里的大人孩子喝西北风去?日本兵也是人,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有啥可怕的?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片甲不留!”
小姨娘兰花指怒指篱外,水杏眼陡生凌厉,粉面含威,莺语吐剑,旋身,摆腰,蹲胯,着竹青色绣木莲的楚楚衣衫的小女子,刀剑之气顿生,威风凛凛,不啻于戏台上蟒袍凤冠、威风凛凛、挂帅出征的穆桂英。
小姨娘就是戏台上的穆桂英。
二姥爷说:“小苍兰呀!这个乱世,可不是女儿家逞能的时候,虎狼之兵,避之唯恐不及!镇子上的女孩,拿草木灰把脸蛋抹得像锅底,个个躲在家不敢上街。那畜生一样的日本兵,啥事做不出来?”
姥姥走出来,端着苇篾编的馍筐,和二姥爷打招呼:“二弟,在这儿吃早饭吧?弟媳和孩子们可安顿好了?”
小姨娘回身看一眼,姥姥依旧梳洗得清爽利索。青布的衣裤,白生生的脸上不搽一粒脂粉,细纹荡漾,平添了几分慈祥和安静。脑后的大纂儿,漆黑油光,斜插着一根带流苏的银簪,明晃晃的,亮亮的。那是小姨娘昨儿拿香胰子水刚洗过的。
二姥爷恭敬回应着:“劳烦大嫂嫂了。菊儿他们娘几个,连夜送到十八里铺去了。那里偏僻了些,暂时还没驻兵。”
菊儿是二姥姥,三十多岁,菊花一样端庄秀美。平日里,爱穿白衣裳,性子甜软,在裁缝铺里做老板娘,恰好她娘家姓白,人称白菊花。素日里为人行事,倒是玲珑善良,惜老怜贫,在码头镇上,竟然名头盖过二姥爷。十八里铺,是二姥姥的娘家。
三
早饭。稀粥、腌青萝卜条、野蒜炖咸肉、杂合面猪油葱花卷子。小姨娘唱戏,姥姥侍弄两亩薄田,日子比一般庄户人家要富裕好多。三个人坐在老杏树下,围着木头桌子,边吃边说话。
头上的小青杏不知何时变黄了,暮春即将唤醒初夏。人间绿了起来,庄稼地里也淌着绿,空气里散发着绿色的清香。
二姥爷呼噜呼噜喝着稀粥,感叹着时间过得真快!说地里的麦子抽穗了,今年阳光雨水都充沛,眼看着要有一场几年不遇的好收成。
“唉!眼瞅着到嘴的粮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囤里去。日本兵在西边打了败仗,缺了粮草,饿皮虱子似的。谁知道驻扎着不走,是不是想望着咱的粮?”
小姨娘一片一片撕着卷子,慢慢往嘴里放,若有所思:“二叔,咱的部队呢?咋不过来把这群饿狼给剿了?”
二姥爷复又长长叹口气。接着,摆一摆手,示意她们娘俩凑近些,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小声说:“小苍兰,你知道的,菊儿的大侄子,叫白川柏,和你年龄相仿的那个,你记得吧?在咱部队里是个侦察连长呢。前一段时间,菊儿偷偷往部队上送军鞋,听川柏说,他们接了新任务,完成后,很快就赶过来。具体啥时候来,属于军事秘密,没说。”
仨人继续喝汤,吃咸菜。清脆的萝卜条被嚼得咯吱脆。那声音里,分明有欢喜,有快意。
小姨娘抬头望,篱角的一棵白檀,满枝头的绿,捧着一窝一窝的白,碎碎的白花瓣里,伸出鲜嫩的淡紫色的花丝,像白衣裳的女孩,臂弯飘着的丝绸带子,清新清甜的模样,像画报上民国的女学生,楚楚的。
碧空也染着绿,小姨娘看到绿绿的云在天上生长,像长了一丛一丛的野豌豆。
季节到了最美的时候。倘若没有从东洋小岛上跑来的强盗,我们的家园,该是多么清宁静美啊!
四
姥姥问:“镇子上迷失的女孩子,张记酱园的姑娘,找到了吗?”
二姥爷不说话,手里的竹筷停在了青花瓷盘上,一根青碧的萝卜条,夹着,顿住了。
啪——竹筷摔在瓷盘上,一根绿萝卜条,掉出去,柔软的腰身,变成了一柄小利剑。
姥姥和小姨娘被吓了一跳。抬眼,看见二姥爷的脸变成了腌菜色,青黑,挂霜。
“那女孩惨啊!多好的女孩子,孝顺,懂事。眼看着收了麦,就嫁人了……”二姥爷喃喃道。
“老张头雇人打了一院子红亮亮的嫁妆。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置下的家业,不给独生女儿,给谁?未来的姑爷人也不错,老张头不嫌贫爱富,看中的是他憨厚能干,心地善良。他原是酱菜园里的小伙计……”二叔手掌根大力蹭了两下泪水麻花的眼睛。
“一对年轻人情投意合的,眼看着就要结为恩爱甜蜜的小夫妻了。谁知道那帮狗杂碎,干了这么伤天害理、猪狗不如的事……”
二姥爷哽咽,半碗稀粥冷成糨糊。实在难以下咽。
五
张家姑娘的遭遇是这样的。原来,那天夜里,老张头的哮喘病犯了,脸憋成了猪肝紫。而小伙计又偏偏被老张头打发回乡下,给孤寡老母送干粮去了。
这些日子,镇子上驻的兵,披着黄狗屎一样的皮,呜哩哇啦满巷子乱窜。家家户户惊惶不安,关门闭户,特别是那些有妙龄女孩的人家,恨不能撅棵大树当门栓,生怕野兽窜进来吃人。
可张家丫头不能眼睁睁看着爹爹命悬一线呀!于是,心一横,出门了。她脸上抹了厚厚的草灰,身上穿了件奶奶灰不拉几的布衫,腰上缠了个爷爷油渍麻花的褡裢,头上戴了顶爹爹脑油深厚的毡帽,打扮得像要饭花子似的,猫腰钻出了院门,遛着墙根往街西头药铺跑。
明晃晃的大月亮下,一队醉醺醺的日本兵迎头过来。女孩藏在人家墙外的一蓬野栀子花下,大气儿都不敢出。到底还是被对花撒尿的一个兵发现了。可怜的女孩,小白兔似的,被揪了出来。
喝红了眼的日本兵,推推搡搡,戏耍着猎物,而且是一只吓傻了的美丽猎物。
在一阵阵狞笑声中,月亮不忍看,躲在了一片云彩后……第二天,人们找到的是张家姑娘冰冷赤裸的身体,躺在小巷尽头的一蓬野栀子花后面。身下枝折花凋。大朵的栀子花揉碎在绿绿的草地上,白花,染成了红花……
小姨娘眼底渐渐蓄满了泪水。她悲怆唱出:“夫死子亡心已碎,血海深仇压双肩。今日重披连环甲,不少狼烟誓不还!”
姥姥和二姥爷知道,这是《十二寡妇征西》中穆桂英的唱段。
他们任桌子上羹菜冷,心头火焰升。看小姨娘脱去女儿裳,披上戏袍,手里一根红缨枪,小小的篱落里,翻袖,挺身,提神,长枪挥舞,战袍翻飞。
二姥爷以竹筷为槌,木桌为鼓;姥姥以瓷碟为锣,手指为棒。叔嫂二人紧锣密鼓。一霎时,战鼓声声,唤英雄。小姨娘望见他俩的眼珠亮了一下,像很远的星光。
六
篱笆院里的石榴花开了。
那藏在油汪汪绿叶间的点点殷红,最是暴露了它们按捺不住的心思。花间突然一声鸟叫,不清脆,喑哑的,却很有穿透力,有点像姥爷的声音。
那一声鸟叫仿佛刺进了小姨娘的身体,她觉得浑身的每块肉每根骨头都被鸟叫惊醒了。
整个篱笆院静静的。阳光筛落的花影,刚刚还小银鱼似的,在地上蹦蹦跳跳,此时,也拓印成一幅静止的画。唯有那只很大的鸟在叫,声音孔武有力。
七
夜里。月亮明晃晃的,像莲花,像白果,更像一个女孩的笑脸。那是张家姑娘的脸庞吗?杏眼如星,脸若银盆,戏词上说的好看女子。张家姑娘就长成那模样。
小姨娘熟悉那女孩,常常来戏园子听戏,嗑着瓜子,闲淡地倚着红漆剥落的柱子,也不坐。一根粗黑油亮的大辫子,搭在隆起的胸前。喜欢穿淡竹叶色的斜襟盘扣布衫。安安静静的,小门小户的,像一朵清素的槐花,锁着春色,藏着羞静。一站,就是一幅碧玉图。怎能不令小伙子萌生和她成亲的念头?娶回家,一定是贤淑能干、知书达理的妻。
小姨娘想起张家女孩的惨状,简直是一朵清白芬芳的花朵,尚未绽放,硬生生被拽下枝头,碾落成泥。怎不令人摘心摘肺般的疼!
恍恍惚惚中,月亮越来越模糊,姑娘皎洁的笑脸也越来越模糊。月亮周围起了风圈。以后的几天,都会有风。
梦里落英缤纷。小姨娘看见了姥爷。
仿佛儿时窝在他宽大温暖的怀里,闻着他薄薄的烟草味。小女孩仰起头,看见姥爷宽大的胸脯和满是胡子的大下巴。
姥爷抱着小女孩唱一段。那浑厚的唱调是从胸腔子里跑出来的,震得伏在他胸膛前的小女孩像一朵小花,春风里扶不稳。姥爷是武生,一身好功夫,一副好嗓子。“梨香园”的台柱子。
后来,姥爷死了。
那次唱《岳飞抗金》,人入戏,太激动,一个鹞子翻身,却翻到了台下。当场人就不行了。
临死,姥爷拉着小姨娘的小手,交到戏班子师父手里,哆哆嗦嗦留下四个字,就溘然长逝。
四个字,长在了小姨娘心里,生根,发芽,茁壮,葳蕤。伴随着嫩嫩的小姑娘长成如花女子。
岳飞的老母亲血淋淋一字一字刻进儿子的肉里。姥爷把它们一字一字刻进了女儿的心里。那四个字就是:精忠报国!
八
“梨香园”开张了。因为日军头目松井一句话:“东亚共荣!”他强制镇子上一切恢复如常。
镇子上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试探着,像蜗牛小心翼翼伸出触角。还好,日本兵似乎规矩了一些。人们的心稍稍轻松一点点,但还没有从嗓子眼儿直接放进肚子里。他们知道,日军兽性发作会令人猝不及防,绝不能相信他们那一套“东亚共荣”的鬼话。他们是魔鬼,哪里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不过暂时扯一片假惺惺的虚伪面纱,遮掩狼子野心罢了。
虽然街上人多了些,但每张脸上都飘着未散的惊恐,写着“提防”二字。心里的篱笆和家里的篱笆,牢牢扎紧,没有丝毫懈怠。曾经被狼咬过,谁知道狼什么时候还会张开利齿!
想一想,那些日军没来时,镇子上家家门户洞开,鸡狗安详。多好!
可他们来了!如狼似虎,闯进别人的家园,制造战争,制造血腥,把人间变成地狱。这世间,被他们蹂躏得如此寒凉,如此疼痛。所以,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在萌发。
停了月余的戏园子,有些荒寂。蜘蛛在廊角安居乐业。小姨娘种下的牵牛花,在戏台子一角,倒是热闹。一进门,气势磅礴地扑过来,红红白白,蓝蓝紫紫。
戏班子里的人像压抑良久的草木,一进园子,全都抬起了腰身,返青,活泛,眉眼里都是活力。大家忙忙碌碌,脚步轻盈,该打扫的打扫,该归置的归置。班主给大家开了个会,说咱们该唱戏的唱戏,只是把那些日本人敏感的戏,暂时先收一收,只唱些情爱的呀插科打诨的呀罢了。日本人也会装模作样来听,他们里面有中国通,比如那个日军头目松井司令,就特别喜欢中国戏。
“胳膊拧不过大腿。大家暂且先忍一忍。这些东洋鬼子,很快就会被咱们的队伍收拾的。”班主狠狠地挥了挥拳头,眼圈红了红。
大家也暗暗攥了攥拳头,眼睛热了热。
他们想起了这一个月里,镇子上那些日本兵的兽行,特别是张家丫头的事,是每个人心头的一道坎,过不去。咋能过得去!
九
小姨娘在后台,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红菱子旧手帕擦去台子上、镜子上厚厚的尘土。菱花镜子里映出她上半个身子。
镜子里的女子,清瘦、灵巧、玲珑。分明是中原女子,却有那种青山绿水间女子的小巧与俏丽。有妩媚的娇嗔,有果敢的凌厉,灵秀楚楚,心似兰草,清丽可人。
想到马上就能唱戏了,小姨娘的心情好了起来。初夏的阳光,照到心底去了。你看,戏班子人人脸上也不知不觉焕发出笑容来,竟都是一脸春天的模样。
这些唱戏的,不光是靠唱戏养家糊口,更是打从心底热爱啊!干一行,爱一行。他们都爱得要命!停了一个月的戏,简直像草木都要渴死了,锣鼓点一响,都如枯木逢雨,又活过来了。戏,不仅是他们的食粮,还是他们的甘霖,是他们的命。
小姨娘想起自己的爹爹死在了戏台上。啊,不,死在了戏台下。自己的师父,唱花旦的春芍,抱病上台,唱《辕门斩子》。结果,一口鲜血喷在雪白的长袖上,人像一只美丽的蝴蝶,翩然匍匐,以绝美的姿势,香消玉殒。他和她,都是为热爱而献身。
手握眉笔的小姨娘,开始描眉画眼。她口里轻轻唱起来,声音温柔,挤得出水来。她抬头看向身畔垂挂的花花绿绿的戏服,眼神是永远的春天。
有学徒进来,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跟当年小姨娘学戏时的年纪一般大。青衣短发的小男孩,活像扮上的皂衣茶童。他像平时一样,点上线香,提上新煎的一炉水,给小姨娘沏上氤氲的松子茶。
看着瘦瘦的小男孩,小姨娘的心,突然地软软一动,孩子的这份安静与善良,照得见人世间最原始的淳朴。
文弱瘦小的男孩子,偏偏喜欢唱青衣,偏偏喜欢拜小姨娘做师父。小姨娘也喜欢天分极高的男孩。两人是师徒,更像姐弟。素日里,小男孩不喊小姨娘师父,甜甜亲昵地喊她苍兰姐姐。小姨娘给他取了个艺名:小菖兰。
男孩对这个名字喜欢极了。他说他一定好好学戏,长大了做个小苍兰一样的小菖兰。
学戏很苦。可小姨娘和小菖兰却并不觉得有多苦。这些都是他们心甘情愿去做的。有念想,有希望,内心是充盈的。
小姨娘知道,小菖兰,其实就是小苍兰的别称。
她太爱这个孩子了,真的希望长大后的他,能成为比自己唱得更好的花旦。那时候,日子也太平了,日本兵也早被赶到他们的老家东洋岛去了。戏园子里人们或坐或站,悠闲地嗑着瓜子,喝着茶。臂弯间挎着竹篮的清丽女子,穿梭着,微言软语,低声问询:“新炒的栗子,花生,要不要?”有市声,有戏声,人人脸上一片轻松明媚。倘若是冬天,小姨娘会吩咐他们在火盆里煨上几根黄柏枝。还会在听戏人手旁的紫红桌面上,摆几只黄木瓜,那香气,又香又暖。木瓜虽然常常会被小孩子偷偷揣走,拿回家去自己玩,但她也不恼。反正戏园子后面的菜园里种的都是。多好!
她把生命中的往事抖掉尘土,翻检成戏词。以往的日子多好。清贫点,何妨?小民可不就盼个人间太平吗?
一只蛾子,在小姨娘养的一盆瑞香的叶子上,跌跌撞撞,被脂粉香和花香给香迷糊了。一只睡醒的蜜蜂,在镂空的菱格窗子的缝隙间,喝醉了似的,左冲右撞,想必是被袅袅的线香给醺醉了。
小姨娘笑了。想,等可爱的小东西都爬出来,便是夏天了。夏天,是被虫子们驮在身上的。
十
白川柏来了。
那个年轻的侦察连长,却不是五大三粗的汉子,而是书生一样的儒雅。他消瘦,有盛开的莲花一样淡雅安然的眼神,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硝烟味儿。身为连长,却没有半点杀气。正如戏文中说的:“真正的文人,没有酸腐之气;真正的酒家,没有鲁莽之气;真正的武人,没有刀剑之气。”
小姨娘被他长风浩荡的风雅所倾倒。倘若没有日本人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饱读诗书的白川柏,要么为师,要么为医。这两个职业都是济世救人的。可现在,动荡不安的国家,支离破碎的山河,哪里能安放一张平静的讲桌,一张号脉的药案?投笔从戎,是有识之士毅然决然的选择。驱除倭寇,还我河山,是无数青年的慷慨激昂。白川柏,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他温暖地微笑着,看着眼前的女子。小姨娘在他清澈的眼神里,记忆一下子鲜活起来。
十一
小姨娘和白川柏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小时候,白川柏住在白菊花家。白菊花是他的姑姑,是小姨娘的二婶婶。他俩一起玩耍,后来一起到镇子上的学堂里读书。
二姥姥白菊花开裁缝铺。姥爷在“梨香园”唱戏。
他俩被大人带回乡下时,简直像刚出笼的小鸟,扇乎着翅膀到处飞。乡下广阔的天地,是他们的乐园。
春天的夜晚,俩孩子手挽手,一起到村外的野塘舀鱼。
天上的星星妈妈,生孩子真快,真多。刚刚才有几颗,回头,已经满天。小女孩困了,软软的,细绒毛发的小脑袋,直往小男孩稚嫩的小肩头歪靠。
小男孩唤醒小女孩,高兴地大喊:“鱼儿!鱼儿!水里好多鱼儿。”于是,他们会舀起鱼。有时,会舀起一些星星。鱼倒回水里,星星装进木桶,拎回家。
野塘边的一棵老梨树,开出落雪的模样。
秋天的夜晚,他俩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看月亮。露水打湿了薄薄的衣衫,凉凉的。小男孩就会揽过小女孩,用小小的身体传递给她一丝的温暖。
小女孩问:“月亮里的那棵桂花树,刚刚长好伤口,又被砍开了。那该多疼呀!”
小男孩说:“我就是吴刚,力气大得很。我能把桂花树砍下来,送给你,好不好?你当嫦娥吧。”
小女孩撇一撇嘴,说:“吹牛!你才不是吴刚呢!戏台子上的吴刚力大无穷,有这么高,这么壮!”她站起来,趔趔趄趄,努力比画着。
“一个人,不在于长得多么高大,比的是智慧。学堂里老师说的。”小男孩一双清澈的眼睛里,落进了露水,落进了星星,晶晶亮亮的。
“那我也不当嫦娥。她偷吃仙丹,只想着长生不老,只想着漂亮享福,不管别人死活。爹爹说,她有点自私,不懂奉献,不懂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小女孩小嘴叭叭的,一套一套的,把小男孩说得都佩服起她来了。
“春兰小妹,你懂得真多。真了不起。”小川柏给小春兰竖起了大拇指。
月亮里,吴刚的斧子重重地砍,桂花轻轻地落。人间桂花树下的两个孩子,拾起来的是桂花,拾不起来的是月光。而他俩的对话,在彼此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
十二
岁月缓慢如一片薄云,尚未盖严时间的裂缝,家乡的初夏尚未靠近麦香的芳菲,却招来了一群嗜血的野兽。就是因为那群野兽,白川柏回来了。
小姨娘低头,目光落在绞着帕子的手指上,有些慌乱。好多年没有见面,见面就是俊雅青年。小姨娘的心房怦怦直跳。
初夏的风,从门边挤过来,是草绿色的,吹得人的心里,长出嫩嫩的水草来。耳畔,萦绕着泉水一样的鸟鸣。呀!时光一粒一粒,都是清美的。两个人儿,相对而立,脉脉,默默。时间倘若一直这样水嫩柔软、安详清宁,该多好!
白川柏看着眼前的女子,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这还是多年前,那个伶牙俐齿、天真如雪的小春兰吗?如今,她是角儿,是当红花旦,是戏园子门口贴着的美人像,是小苍兰。
“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他想起多年前,和她站在开成一树雪的梨花下,她仰着鲜嫩的小脸,手里捻着一朵梨花,说出了一句那么美的话。她也许忘记了,他却清晰地记着。这么多年,枪林弹雨中,他负伤,躺在洁白的床单上,周围弥漫着浓重的来苏水味。昏迷中,他眼前出现一片雪白的梨花,一个白衣裳的小女孩在梨花林中奔跑,口中说着那句话:“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浴血奋战中,白川柏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青年啊!随着时间推移,他心中对女孩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开始写日记。在硝烟暂歇的壕沟里,他掏出巴掌大的笔记本,开始和她说话,记下了对她的想念与祝福。满满的一页,密密麻麻,想念、牵挂、祝福,还有每一次打仗的激烈状况。然后,他把小本子放在贴近心脏的上衣口袋里。战斗结束后,他总要嘱咐亲密的战友,说,倘若有一天,他牺牲了,一定想办法找到她,把日记本交到她手上。如果她已为人妇,就不要打扰她,把日记本烧掉。
白川柏此次乔装打扮来到码头镇,身负重要任务。他要侦察驻扎在镇子上日军的军事动态、兵力部署、进攻方向等信息,这些情报对于我军攻打码头镇的战略决策至关重要。他要在镇子上住下来,实地侦察,详细摸清敌人的具体位置、兵力分布、武器装备等情况。同时,作为侦察员,他还需具备高度的保密意识。
可是,他还是来找小苍兰了。白川柏承认,自己有私心,想解相思之苦,见到日思夜想的姑娘。但是,更多的是为这次侦察任务的顺利完成而来。因为“梨香园”一来可以安全栖身,他对小苍兰无比信任;二来听戏的日军多是中上层的军官,更容易获取情报。
所以,白川柏以小苍兰在外行医多年,眼下回归故里的表哥身份来到了“梨香园”。
小姨娘冰雪聪明。况且,她已从二姥爷的口中知道了白川柏的身份。所以,心照不宣,一个字不问。她对班主说表哥回来了,想在镇子上开个中药铺子,在没找到合适铺子前,暂且在园子里住下。
兵荒马乱的世道,班主古道热肠,又加上是台柱子的亲戚,哪有不应承下来的道理。于是,命人打扫出园子角落里的一间柴房,安排他和小菖兰住在了一起。
白川柏住下之后,每天早出晚归。戏园子里人来人往,没人注意他。
每天深夜,小苍兰卸了戏装,看见柴房里一灯如豆,知道白川柏尚未休息,便走去说话。小菖兰十分机灵,看见小姨娘来,他就找个借口溜出去。临走,还调皮地对小姨娘做个鬼脸,轻轻掩上两扇门。
柔软善良的孩子,小小的心里竟装着对师父这般纯粹的爱。他希望她找到心爱的男子,早结良缘。白川柏,绝对是个好男人。小菖兰以孩子干净的眼光,早在心里对这个男子下了判断。而且,从小姨娘娇羞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是喜欢他的。
有时候,小菖兰贴在门外,想听到他俩说些什么,却听到喷着香的笑,笑声轻得似风。那段日子,是小姨娘最开心的时光。她的身上,真的没有了一丝愁云的影子,有的是明朗、是明媚、是明快。
小菖兰希望表哥不要离去,更热切盼望表哥赶紧娶了小姨娘做新娘。
十三
立夏,万物拼了命地生长。花事已过,绿在呈批量繁衍。麦子已吐出绿绿的穗子,绿波倾荡。
时光倘若停留,该多么美!可是,其时的人间,东洋岛上跑来的野兽,虎视眈眈。码头镇的人们正处在饿狼张开的血盆大口里,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
这一天,白川柏来到小姨娘的住处。
小姨娘住在戏园子东北角。一丛翠竹掩映下,一间青砖青瓦的小屋,像一只青色的鸟巢,绿竹依依,把它温柔地抱在怀里。门前一座小巧的红木桥,像垂落的半弯虹。桥下流水潺潺。
白川柏想起来了,戏园子以前是镇子上大财主佟百万的庄园。家财万贯的佟财主无儿无女,死后把庄园留给了侄子。侄子精打细算,一家人住在镇子西头的一处小小房舍里,而把园子租给了戏班子,成了“梨香园”。日本兵没来之前,戏园子生意兴隆,佟家侄子不侍稼穑,不做商贩,靠丰厚的租金,日子富得流油。
竹风送绿,清香浮动。白川柏蹲下身子,看小桥流水里的数尾金鱼,它们的红身子白身子,穿行于绿绿的水草间,如善舞的伶人,长袖飘飘,煞是动人。这使白川柏想起儿时在乡下,他和小苍兰几个小孩,穿着红红白白的衫子,拿着水瓢,蹲在野塘边,舀水玩。一塘的清水,倒映着孩子们的身影,红红白白,像游弋的鱼。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彼时村庄最美的景致。
淡竹叶色的木门,轻掩着,像迷离的睡眼,似醒非醒。屈指轻叩。片刻,“吱呀”一声,房门开了,像两片薄薄幕布缓缓开启。门框里美人亭亭玉立。
看见来人,小姨娘一双水杏眼波光乍现,又惊又喜像小姑娘般的羞涩甜蜜,竟怔住了。
“怎么,不让进去喝杯茶?”白川柏笑吟吟地温声问道。
小姨娘回过神来,侧身含笑往里让。
一脚踏进门槛,才发觉这间小小的屋子仿佛已为兰花的香气所浸透。纱窗竹帘,书案琴台,无不带有清馨四溢的兰香。身畔的人儿,衣裙上也飘散着淡淡的清香。
闲云封户,花瓣沾衣,芳草盈阶,茶香几缕。时光如此静好。白川柏心中涌起一阵豪情:无数战士浴血奋战,甘愿用一腔青春热血,换得世间清宁。他,也是其中一员。
屋里屋外静极了。只有竹影婆娑,只有兰花静放。这情景,使白川柏想起《小窗幽记》里的一句诗:“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倘若没有战争,那么,和心爱的姑娘在此观竹赏月,该是一件多么雅的事啊!
坐在竹藤方凳上,用细瓷盖碗喝着“滇绿”。那小巧的奶白茶碗上,拓印着一朵秀气的兰花。屋子里大大小小摆放着十几盆兰花,看看披拂的兰叶,清秀素雅的兰花箭子,闻着兰花的香气,白川柏一时有种微醺的感觉,真不知身在哪一世。
今天他来访小姨娘,踏进如兰似桂的女儿家闺房,差点迷醉其间,忘了此行的目的。他是来辞别的。今夜,有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倘若顺利完成,他就要连夜离开码头镇,赶往部队。
面对兰花般的姑娘,他实在不忍心让她担惊受怕,尽力装作风轻云淡的样子,只说今夜要回去了,特来告别。
冰雪聪明的小姨娘,捕捉着白川柏细微的表情变化,揣度着今晚他要办的“最后一件事”的危险程度。她不问,不能问。这是他的“秘密”。她明白。
她强颜带笑,轻轻叮咛:“天黑,风大,万万小心。”
两人对坐良久,默默无言。其时,要语言做什么?有两颗滚烫的心,就够了。
分别在即。这一别,山高水长,生死未卜。心中的万千不舍与担忧似波涛汹涌,唯有缄默,怕一开口,就会洪水滔滔,情意泛滥。
“茶凉了。我去续上!”她说。泪珠欲落。
“不必了。我该走了!”他说。语气清凉洒然。
如今情势危急,怎能儿女情长?白川柏一仰头,喝下半盏残茶,眉宇间温情变英气,毅然离去。
小姨娘倚门而望,竹风兰影,人儿站成一幅水墨画,孤清戚然,疏笔留白。
十四
月亮,像一瓣白菊花绣在天上。
“梨香园”座无虚席。多半都是日本兵,还有被强迫而来的乡绅。那些身着绸缎衣裳的男人,带着家眷,战战兢兢,如虎狼在侧,心上惶惶不安,哪里有听戏的喜悦,都是心惊肉跳。
今夜唱的是豫剧名段《柜中缘》。
后台的化妆间里,小姨娘遍身绫罗,满头珠翠,粉面桃腮,却人若冰霜。她心里都是白川柏的影子,都是牵挂与担忧。他今夜去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日本兵如狼似虎,他孤身一人。上苍保佑!愿他圆满顺利,安全脱身。
一旁的小菖兰看小姨娘魂不守舍的样子,想起晚饭时不见了白川柏的身影,聪明的孩子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他不问,不说,默默地陪着小姨娘,不时透过镂空的窗户往后院瞧。那间柴房始终黑漆漆的。他小小的心也黑漆漆的。他多么希望那里面陡然亮起一盏明灯,照亮柴房,也照亮他们师徒二人的心。
戏台上,灯火通明。戏台下,人声喧哗。夹杂着呜里哇啦的东洋话,和他们放肆的笑声。
紧锣密鼓,声声催。小姨娘不得不站起身来,莲步碎碎,如同轻盈的云朵,飘向戏台。每一个小碎步都小雨点般落在观众的心弦上。
明亮的灯光下,只见她身姿袅娜,宛若柳丝。明眸生波,仿若春水。红唇一点,恰似樱桃。桃花粉的袄裙,荷叶翠的坎肩,朱瑾红的手帕,简直像一朵绉缎做的花儿,水嫩嫩地开在赭黄地毯上,明艳动人,直逼人眼。
她唱道:“许翠莲好羞惭,悔不该门外做针线。那相公进门有人见,难免得背后说闲言。又说长来又道短,谁人与我辩屈冤。这才是手不逗红红自染,蚕作茧儿自己拴。无奈了我把相公怨,你遇的事儿本可怜。不向东走不西窜,偏偏来到我家园。我本是女孩人家心肠软,怎忍将你往外掀……”
呖呖莺啼,使人想起《簪花髻·笑和尚》:“啭呖呖,纤柳音摧拍得歌喉絮。”台下掌声雷动。
十五
突然,一声枪响。紧接着,一队日本兵杀气腾腾地闯进戏园子来。
锣鼓琴弦戛然而止。小姨娘闭口而立,像一只受惊的蝉。她脑子里顿时闪过白川柏的身影,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一个日本兵跑到听戏的松井跟前。松井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发生了什么事?”
日本兵附耳咕噜了几句。松井脸色大变,马上招手让翻译官近前来,对他呜哩哇啦说了些什么。翻译官跳上戏台,面向观众,挥舞着手,大声喊道:“刚才,有一个负伤的八路军,逃进了‘梨香园’。请大家不要慌乱,各就各位,配合皇军细细搜查。他身上带着重要情报,就这么个园子,即使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他搜出来!”
小姨娘一阵眩晕。她知道,日本兵要抓的是白川柏。他负伤了!他就在园子里!她心急如焚。白川柏,你在园子里的哪个地方呀?
一只小手轻轻拽了拽小姨娘的裙裾。一回头,小菖兰蹲在她身后。他身量小小,没被人发现,不知何时钻到台上来的。小男孩悄悄指了指幕布下。小姨娘顿时明白了,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那只作为道具的柜子,还没到出场的戏段,本来是掩在大幕后面的,现在却露出了一角。而且,要命的是,柜子下面有一小团鲜红。是血,新鲜的血!那么醒目!他,就藏身在柜子里。负伤的他,血滴在了柜子下。
小姨娘明白了。慌乱中,白川柏跑回了“梨香园”。混乱中,小菖兰把他藏进了柜子里。想不到,一场现实版的“柜中缘”上演了!
怎么办?怎么办?日本兵很快就会搜到戏台子上来,很快就会发现柜子下的鲜血,很快就会把负伤的白川柏逮捕。小姨娘心急如焚。她不再害怕,脑子里飞快想着对策。
没时间了,来不及了。她看见戏台下杀气腾腾的日本兵,蚂蝗一样扑向戏园子的四面八方。有几个日本兵正往戏台子赶来。
永别了!白川柏,来世,我们再续前缘。到那时,我小苍兰一定做你最美最贤的妻。我们在和平的阳光下,煎一炉水,沏一瓯茶,焚香弹琴,琴罢品茗,共读《小窗幽记》。多好呀!
诀别了!白川柏,世间有一种告别,不是无情,而是深情到了极致。小苍兰就是。
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娇滴滴的小家碧玉许翠莲顿时变成威风凛凛的穆桂英。她后退几步,靠近柜子,冲台下怒斥:“你们这群强盗,听好了!想抓八路军,痴心妄想!他早从我给他留好的后门跑出去了!你们这群强盗,闯入我们的家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很快我们的队伍就会消灭掉你们这群野兽……川柏,好好活着,替我报仇啊!”
小姨娘悲怆地唱起《穆桂英挂帅》:“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属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
戏台下,恼羞成怒的松井,嚎叫着,命令日本兵齐齐开枪。戏台上,小姨娘像一只美丽的蝴蝶,翩然扑落在柜子上。鲜血染红了青色的幕布,从柜子上流下来,和柜子下白川柏的血交融在一起。他俩的血,玫瑰般鲜艳,多像她梦中做他的新娘时,娇艳艳的红盖头……
十六
许多年以后。
清明。杏花微雨。一个眉眼和小姨娘相似的女子,来到一座小小的坟茔前。坟前竖着狭小的石碑,石碑上简简单单刻着五个字:“小苍兰之墓”。
我把一抱洁白的兰花,放在碑上的名字前。兰花和兰花紧紧相依,清香弥散。
春天的田野,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这里的树木枝头已绿意轻点,手挽手,肩并肩,围成一道清绿的屏风,把小小的坟茔宠溺地抱在怀里。一条野渠候在坟前不远处,清清亮亮,像守望的明眸里面蓄着一往情深。大片的芍药,正脉脉打蕾,几场春雨洒一洒,就会扑棱棱开成一片云蒸霞蔚的红,喜气洋洋的,像新娘子的嫁衣裳。
我掏出怀里的一个小本子。年深日久,它已被血渍和光阴浸染成暗褐色。我把它放在墓碑下的兰花丛中。那是白川柏的日记本。他在牺牲前交给了小菖兰。
当年日本兵撤出戏园子,小菖兰和戏班子的人,把昏迷的白川柏从柜子里抬出来。安葬了小苍兰,他跟着白川柏一起去了部队。白川柏牺牲后,这个小小的日记本,小菖兰一直珍藏着。直到病逝前,才嘱咐家人辗转找到我,把它郑重交到我手上。
一个月亮,守望一个村庄。一个女子,守护一颗兰心。一个本子,诉说一个故事。小苍兰的墓碑前,风儿正轻轻翻开一本旧日记。春风它识字?看得懂纸页里的深情,读得懂那些岁月留下的印记?风动花香,它只管来去,不问归期。
我的小姨娘呢?一个兰花般绝美的女子,以最纯净的姿态来过尘世。她,等到白川柏的归期了吗?
【作者简介】朱盈旭,笔名梅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海外版》《草原》《安徽文学》《广州文艺》《红豆》《星火》等刊。获第四届吴伯箫散文奖一等奖,第一届教师文学艺术奖·散文奖。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