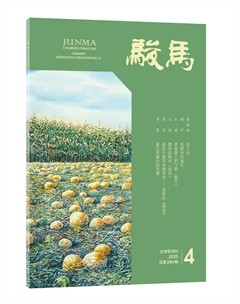一
那时我尚且年轻,没有拿到任何文凭,骑着自行车在B城像一只无头苍蝇乱飞乱撞。四处找房子,雄心勃勃,想开一家私人幼儿园。樊家巷,我曾经几次深入驻足,看信息栏里的房屋出租信息或者招聘启事,妄想跳出那个石油小镇,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个咸鱼大翻身。八年后,盲目的我再次来到了这里,只是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年轻和勇气,只想在城市的一隅躲避尘世,经营花店,读书写字,像八年前一样,纯真烂漫。这时,我对这座城市依然一无所知。
樊家巷在城区中心、渤海八路中段东面,是一条又窄又长的巷子。市场的北边有卖猪头肉的、卖炸货的、卖青菜的、杀鸡的、烫发理发的等,市场的南边有卖馄饨、水饺、面条的,还有卖拖把、茶壶、水果的等,都是从渤海八路到渤海七路一字排开,简直像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在我没有来到这座城市前,樊家巷就这么热闹着、繁华着,我来到这里后,它依旧是往日的面孔。
这儿的商品加起来可以顶上一个大型超市,商品仔细排列可以排满半个B城。这是一条很陈旧的巷子,出租屋低矮、破旧、狭窄,街道上坑洼不平,空气也不怎么新鲜,只是因为给周围的居民提供着日常的方便,所以一直平安无事地存在着,也可以说有存在的必要性。开着奥迪的男人会停下车,买几两猪头肉下酒,时髦的女人也会把细高跟印在樊家巷并不怎么干净的路面上。
农贸市场的存在,让我对于城市的印象“大打折扣”,可以说和我想象中的城市相差甚远。从这里往西,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现代化新城版图,但是冥冥之中,我却来到这样的一条街道落足,并完成了在这座城市的行走。樊家巷584号就是我花店的位置。想想命运将我安排在这里一定有它的道理。这儿是最平凡的民间,最热闹的俗世,最细微的生活。上苍给我关闭了在石油小镇的大门,却给我打开了樊家巷这扇民间的窗户。
二
诸多农民将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带到我花店附近的街道上来卖。有时来个卖大白菜的,那白菜头颅浑圆,一看就是勤快人种植的。有时来个卖豆子的,豆子装在布袋里,一小袋一小袋地排列在马路牙子上。打着红色包头的老妇一点儿不觉得掉价儿,反而坐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静静穿针引线纳鞋底,那姿态真让我羡慕。有问豆子的,她就放下鞋底,双手捧起一些豆子,有时是红小豆,有时是绿小豆,有时是大黄豆。豆粒翻滚,在阳光下散发出粮食温暖饱满的光辉。这些粮食让她自豪,似乎是她培养的可以上清华北大的孩子。
有一天,来了位七十多岁的大爷,我和花店隔壁的厨师们都叫他菜爷。菜爷穿米黄色西服,戴黑色廉价针织帽子,帽尖空空的,让我觉得里边充满了寒冷的空气和风。脸上皮多肉少,皱纹深刻,眼睛凹陷有神,双手爬满了蚯蚓般的褶皱,是消瘦的干枯的那种蚯蚓褶皱。他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上的两个灯泡硕大明亮,显得他更加衰老暗淡。车上是他自己种的蔬菜:捆好的一小把儿一小把儿的香菜和一大把儿一大把儿的小白菜,塑料袋里是散装的小油菜,一块板子上是几个腌咸菜的辣根。六把香菜一字排开,身材修长,鲜嫩生香。小油菜七八把或者更多,堆起了一个高度,翠绿欲滴,看着就想拿虾米与小油菜炒来吃,既安全又绿色。
大爷挥舞着他的蔬菜,对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用嘶哑沉稳的嗓子喊:新鲜的香菜、小白菜便宜了,便宜了,纯天然绿色无污染不打农药,上面还有虫子眼儿……香菜一块钱一把儿,小油菜五毛钱一把儿。大爷喊出的价钱,或者他说的蔬菜上还有虫子眼儿的这句话,牵动了坐在花苑里读书的我。长期的饮食不规律与吃带农药的蔬菜,早已经让我的肠胃千疮百孔。蔬菜带有虫子眼儿说明洁净到连虫子都喜欢吃。虫子喜欢吃的就是适合我吃的。
他的喊声也把我喊回到夏天。夏天的蔬菜才会这么便宜,冬天的蔬菜价格一路飙升,往往让人望“菜”生畏。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把儿香菜,可以分五次吃,花了五角钱买了一把儿小油菜,可以分两顿炒。我拿走大爷三轮车上最后一把儿小油菜时,他接着从三轮车兜里拿出了另外一把儿,再接着又拿出一把儿,似乎他的车兜里有无穷尽的小油菜,或者说他的蔬菜通着他的土地。
菜爷的身边是喧闹的都市霓虹,飞扬的垃圾尘土,头顶上是渐渐降落的夜色。而大爷似乎功力非凡,在道路旁,我的花店门口,能持续站好几个小时,喊好几个小时。喊着喊着,夜色裹着冰冷重重砸在他的身上;喊着喊着,他的蔬菜越来越少,最后的几把儿注定蔫了被他带回去当作晚餐。最后,他的喊声只有自己能听见,嘴里哈出的白气再也冲不开寒冷。街上没有了行人,只剩他像一个僵尸一样站立于路旁。我甚至担心,要不是我门口那根电线杆的支撑,他也许会倒下去。但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副在土地上练就的骨骼是不会轻易倒下去的。就像我的父亲,都七十多岁了,还在麦收的季节,到田野里弯腰捡拾遗失的麦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