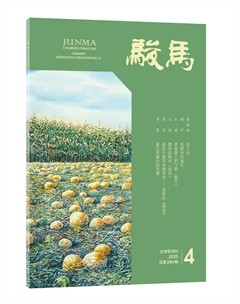你又一次在梦里亲吻了我,这不稀奇。亲爱的阿列克谢·科兹洛夫,你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十九年零三个月了,虽然我已能隐约地听见死神对我的召唤,但是我仍然顽强地活着,就是想着有一天能把你那被子弹穿透的身躯带回安哥拉河畔,你和我在上帝的见证下永世长眠。
战争是魔鬼,是一切罪恶的来源。1945年的初夏,盟军胜利的消息从莫斯科传到赤塔,人们高兴坏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乡村停产,大家围坐在一起拉响巴扬琴,喝干了酒窖里存下的美酒,等待着我们的英雄凯旋。在舞会上,你像一棵白桦树一样踩着鼓点儿来到我的身旁,悄悄地对我说道:“玛格丽塔,战争结束了,咱们把婚礼定在麦子丰收之后吧。”我顿时羞红了脸,这让一旁的乌里扬娜听到了,她是个大嗓门的姑娘,立刻伴着琴声唱道:“漂亮的姑娘要当新娘,新郎要备足黄油和蜜糖,祝福他们生活像美酒,要生下三个儿子还有两个姑娘。”乡亲们将手中的伏特加一饮而尽,大声地祝福我们。但是谁也不知道好日子和坏消息究竟哪一个先到。就在我和阿列克谢筹备婚礼的时候,后贝加尔方面军军部向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出了征兵消息,我的阿列克谢也在去往中国海拉尔前线的名单之内。他将在1945年8月9日,跟随“光头将军”格里高利·列武年科夫率领的步兵八十六军开赴海拉尔战场。
临行前的头一天,阿列克谢采了一大筐的野玫瑰来到我的家里。我还记得他一边为我编着玫瑰花环一边说:“人们都说战士的血里有风,注定要征战漂泊。但你不要担心,我们是和中国的部队一起打日本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等我回来做我的新娘吧。”他把编好的花环戴在我的头上,告诉我这是这个夏天最后盛开的野玫瑰了,希望能给我们彼此带来好运。
我凝视着他淡蓝色而明亮的眼眸,身上的香水味伴随着微风吹来,我不禁在他讲话的时候亲吻上去。就是这一吻,仿佛是一杯爱的香油,浇在了阿列克谢干涸的心脏上。我永远都忘不了,他那炙热的红唇像开了窖的甜酒,平时不善言辞的舌头此刻化身为一条灵活的小蛇,在我的鼻尖、上颚、下巴尽情地游走。他将我抱起来,让我的靴子踩在他的皮靴上,我轻闭双眼,肆意享受着阿列克谢带给我的爱。突然,我家的黄狗布塔轻吠了几声,随后马车的铃铛声由远及近,我知道这是父亲割草回来了。被坏了好事的阿列克谢拿着一条板凳就要去打布塔,被我拦下,我对他说:“爸爸回来了,布塔是我窗下的‘哨兵’。你放心吧,我的小伙子,我就是这夏天里带刺的玫瑰,只对你这只勇敢的‘蜜蜂’开放,等你回来娶我。”
送他去战场的时候,我穿了他最爱看的布拉吉,戴上他送我的玫瑰花环,我哭着说:“把这玫瑰花环剪成两半,一半你带走上战场,就仿佛是我在你的身边。”在他探出卡车外接花环的时候,我当众亲吻了他。人们都说我的阿列克谢艳福不浅,有“瓦茜丽莎公主”一样漂亮的姑娘在等他回来。当卡车开动时,他一边向我挥手,一边将拆下的玫瑰花环轻轻地放进行李中。我看见他身边坐着的依次是安德烈、巴图·耶夫、米里亚、阿廖沙和康斯坦丁诺维奇……
接到阿列克谢战死的消息是在两个月后,赤塔下了第一场大雪。后贝加尔军区的长官,将他的阵亡通知单、卫国勋章和生前的遗物交给了他的母亲。他的妹妹维拉说:“告知阵亡通知的三位同志很平静,只是简单地宣读了哥哥的牺牲消息,说后贝加尔方面军已经将他和其他牺牲的同志上报给了西伯利亚军区,他们都会获得卫国英雄的荣誉,也会给烈士的家属在赤塔工厂安排工作,但名额只有一个。”
我无法掩盖内心的悲痛,疯了一样跑到阿列克谢的家中,看见她的母亲正坐在椅子上,怀里抱着他生前穿过的靴子流泪,地上散落着刚刚烤好的列巴。显然,这位可怜的母亲觉得天都塌了下来。我来到他的房间,扑在他的床上啜泣着,羊毛军衣上还有他撒过的香粉味儿,就像他送我的玫瑰花的花香,我仿佛又感受到了他炙热的胸膛。回去的时候,他的母亲交给了我一个羊皮面的本子。“玛格丽塔,我的好姑娘,这个也是同志们送回来的,我认字不多,你应该把它拿回去,但愿你不会忘记我的儿子。”我把羊皮本子捧在手里,翻开去看,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每一页纸的中间都粘上了一朵干瘪的玫瑰花。这是阿列克谢在战场上写的日记,虽然不多,却是我活下来的动力。
“1945年8月8日,天空下着蒙蒙小雨。我离开了母亲、妹妹还有我爱的玛格丽塔,跟随着八十六军九十四师向东南方向的战场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