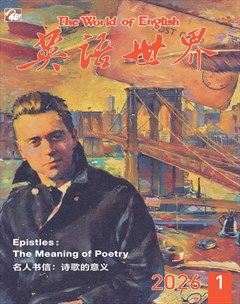【导读】
该信件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1795—1821)于1818年2月27日写给其朋友约翰·泰勒(1781—1864)的。泰勒是英国出版商、散文家和作家,他以出版济慈和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约翰·克莱尔(1793—1864)的诗作而闻名。济慈与泰勒之间有15封通信留存下来,笔者选取的是其中最有名的信件之一。
在该信中,济慈主要谈了自己的三条诗歌原理(Axioms)。第一条:“诗歌应该给读者带来惊喜,然而是通过一种精巧的超越,而非通过追求奇异怪诞。”也就是济慈认为诗歌应该是以读者为中心、以读者感受为导向的,读者读完诗应该感到眼前一亮、感到惊奇或意想不到,乃至拍案叫绝。如果读者读完诗后感觉味同嚼蜡,或如同喝了白开水,甚或云里雾里,那诗歌便没有实现其功能,诗人也没有完成其使命。这一点笔者非常赞同,因为当今时代,有些诗歌是完全不顾及读者的接受力和感受的。济慈认为制造惊喜的手段是通过对前人精巧的超越,也就是要努力克服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卢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而不是通过追求奇异怪诞,甚至走向荒诞不经、哗众取宠的极端。当然这只是济慈本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之一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的诗歌便具有奇异怪诞的特点,譬如其代表作《古舟子咏》(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济慈继续写道:“诗歌应该让读者觉得它表达的是他自己最崇高的思想,它的出现能勾起他的回忆。”这句话看似是独立的一条原理,其实是第一条原理中“以读者为中心”这一话题的延续。这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好的诗歌应该是广大读者的“嘴替”,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但是诗人能够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通过艺术加工,运用诗歌手段,用一种凝练、升华、诗性的语言将普罗大众的情感表达出来,言他人欲言而不能、不会或不敢言的,从而使读者读后产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强烈共鸣。
第二条:“诗歌对于美的营造决不可浅尝辄止,这样才能让读者为之屏息震撼,而非仅仅感到满足。”济慈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强调诗歌在感官上应给人以美的享受,长期以来他被西方评论家看作是唯美主义的先驱之一。在其著名颂诗《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中,济慈明确提出了“美即真,真即美(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的著名美学论断。在1817年12月22日写给两位弟弟的信中,他写道:“对于一位伟大诗人来说,美感胜过任何其他的考虑,或更确切地说,它让人忘却一切考虑。(The sense of Beauty overcomes every other consideration, or rather obliterates all consideration.)”在这一条原理下济慈顺便谈到了该如何在诗歌中运用意象(image):“意象的使用应该像日出、日行、日落一样自然”。济慈是一个非常善于在诗歌中使用各种意象的诗人,包括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味觉意象、触觉意象、动觉意象等,被评论家誉为“感官诗人”(sensuous poet / poet of sensuousness)。济慈信中是在强调要自然而然地运用意象,而非生搬硬套,强行为之。关于意象之于读者的感受,他用太阳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像阳光照耀在读者的身上,最后又庄严地落下,但却堂皇壮丽,让他沉浸在黄昏的奢华感中。”
第三条:“如果诗歌创作不像树木生长叶子那样自然,那还不如不要创作。”这一条是顺着济慈的意象观而言的,他认为不仅意象的使用要自然而然,诗歌的创作本身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这其实是对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著名诗歌理论的一个呼应,即“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涌露(All good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也就是诗歌要有情而作、有感而发,而不能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更不能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