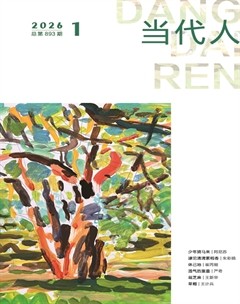一
天没亮,王槛靠着炕沿又在讲他的梦。
他说:“一群孩子,身上披挂五谷,头上生出藤蔓。他们拉我的衣袖,扯我的衣襟,缠磨了我一宿。”
王槛住东屋,我住西屋。他像鱼一样游进堂屋的时候,我就醒了。堂屋没有一件发亮的摆设,王槛还是被黑暗绊住,停留了片刻。
十岁那年,村里的风言风语吹进我的耳朵,说我与王槛、郄进芳两口子没有丁点血缘关系。那以后,我再没有真心真意地叫过他们爹和娘。当着外人,躲不过,我嘴上叫了,心里却默念他们的名字各十遍。那一刻,我灵魂出窍,心无旁骛。为此,我撞过南墙,摔过跟头,有一次还险些掉进河里。
听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说着不着边际的话,我并不惊讶。老辈人惜地,散落在村内的大小地块都有名字,好像轻轻一声唤,土地的精灵就会破土而出。王槛说过,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地主家做长工,每年看秋,看过玉米、高粱、大豆。有一年,看的是红薯。他爷爷爱喝酒,葫芦里灌的是烧锅的酒稍,每晚就着清风明月下酒。一次睡到后半夜,迷迷糊糊中听到咕咚咕咚的吞咽声,他爷爷悄悄起身,看到月光下一个光屁股小孩正抱着他的酒葫芦喝得香甜。喝完了,摇摇晃晃走几步,一跳,没了踪影。一壶酒,每人一半,夜夜如此,直到霜降。那年,红薯大获丰收。只是,煮熟的红薯有股浓烈的酒香。那段时间,地主家的人和牲口都昏昏欲睡。王槛对我说过,对着土地,别骂娘。
屋里没开灯,灯绳断了。
我趴在炕上,三月的晨风吹着苇席印在我后背的纹路。苇席是郄进芳编的。她活着的时候就爱编席。睡在她编的苇席上,我就像只蚂蚁睡在一片树叶上,在河里飘飘荡荡。如今,这感觉依然没变。
“孩子是不是有六个?叫作榆树台、柳树沟、羊角弯、东河岸、西河岸、沙滩?”
“嗯。”
“它们是不是都是‘地’字辈的?”
“嗯。”
“还有块地叫上寺,你怎么忘了?那是咱们旧三队的体己地。那块地要建光伏电站了。地都征了,每亩地八万块钱。二十五亩地,二百万。旧三队十五户人家,八十三口人,分地的时候怎么就少了咱一家?当时咱家五口人,能分一亩半地。当时你是队长,你说是为啥?”
往常,话到这儿也就断了,我们坐等窗外的鸟鸣把我们从沉默中打捞上来。晨曦中,墙上的挂历落满了灰尘。
那天,王槛的嘴里却突然蹦出三个字:云溪寺。接着又说:“云溪寺的老和尚爱收干儿。门口有副对联‘座上泥佛陀,槛外真菩萨’。每收一个干儿,就给干儿对联上的一个字。”说到这里,王槛笑了两声:“轮到我就叫了槛。大年初一去给老和尚拜年,上联东,下联西,老和尚居中坐。那时候,你奶奶常把头梳得溜光,倒腾着一双小脚,穿过村外的杨柳林,一头扎进云溪寺。为这,没少挨你爷爷打。”
我说:“说说地的事。”
王槛说:“前两天,我还去寺里给老和尚磕头。云溪寺的香火不断,同天上的云彩连在一起。老和尚叹息说,五字联不好,要是七字联就好了,就能多收几个干儿。”王槛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后,一位年轻的医生曾对我说过,这种病就是记忆的明灯在逐盏熄灭。只是,关于上寺那块地,他记忆的明灯过早熄灭了。
我用这句话不止一次搪塞过李彩虹。我回村后,每晚我们都会通话。她半是无奈,半是胁迫地说:“房主说再等我们两天,就两天啊。再不交钱,房子就卖给别人了。”我们的儿子王通在市里的一家车企上班,普通工人,车间拧螺丝。处了几个对象,都要求市里有房。可动辄百万的房价就是现实丢给我的一个白眼。看了一套二手房,房主急着出手,房价压到每平方米七千。小区的位置和房屋的布局都不差。电话那头,李彩虹的嗓子又哑了。她十天有九天这样。
我还用这句话搪塞过村书记王辉。不过,他不吃这一套,瞪着眼,说:“七天公示期。七天之内你拿不出证据,等公示期到了,征地款马上打到户主的卡里。到时候,你说啥都是白搭。”王辉是我没出五服的哥哥,头戴两顶乌纱帽。
二
我去商店买盐,路过王辉家门口,被院墙外一棵盛开的梨树吸引。我怀疑王槛就是被这一树的白蛊惑,才嘴里嚷着,下雪了,下雪了,把一袋盐撒得满院都是。王辉端着碗,蹲在门口,问:“我叔最近怎么样?”我说:“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