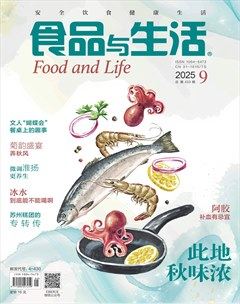苏州糕团的双重价值
上周,我去江苏苏州参加由苏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和苏州图书馆、苏州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一场茶会。茶会主题很“江南”——“字里行间说苏州”,嘉宾有苏州知名作家王稼句、华永根和“打酱油”的我。苏州图书馆的美女主持贾珍在开场白后,无比丝滑地将话题引向了苏州茶食。
华永根先生告诉大家:“苏州人至今对糕团的品赏仍然是‘与时令同步, 与风俗相连’—— 农历正月吃元宵, 二月初二吃撑腰糕,三月清明时节食青团,四月十四轧神仙吃神仙糕,五月端午吃粽子,六月食糍团,七月吃豇豆糕,八月吃南瓜团,九月重阳节吃重阳糕,十月吃萝卜丝团,十一月吃冬至团, 十二月辞旧迎新吃糖年糕。在岁月中等待美味的轮回,便是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守。”
王稼句先生认为,从历史上看,全国范围内没有一座城市像苏州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糕团店,旧时著名糕团店如“黄天源”“颜聚福”“乐万兴”“谢福源”,有“四庭柱,一正梁”之说, 这是稻米文明相当发达的证明。随着苏州的经济发展,商贸活动频繁,作为商务洽谈和休闲场所的茶馆越来越多,糕团自然而然地进入茶馆,成为茶食界的重要角色。
我则从上海人的角度谈点体会:上海人是苏州糕团的粉丝,商业街区和居民集聚地都会开设一两家糕团店,南京路上的“沈大成”和“王家沙”以及开了不少分店的“五芳斋”“乔家栅”, 都是有点年头的老字号,但他们的源头都在苏州。每逢重要节气,上海市民都会去老字号排队购买青团、绿豆糕、双酿团、重阳糕、八宝饭等,足见苏州人的雅致生活对上海人的深刻影响。
在一百年前上海城市化的背景下, 苏式糕团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疗饥解馋,也在于精神上的慰藉和象征。比如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就说:“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雪白的粉墙, 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糍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
糕团界的父子双档
茶会结束,我与国斌兄沿着十全街西行百余步,去拜访一位糕团达人汪成先生。汪先生的祖上是扬州的大家族, 到他父母一代就迁来苏州定居。汪先生长我几岁,他中学毕业时适逢特殊年代,就去农村“修了十年的地球”,回城后在一家电扇厂工作。汪成本是一个吃货,在家也经常下厨练手。为提升自己的烹饪技艺,他遍访城内外名师, 在“黄天源”学做糕团,在糕点二厂学做饼,在“得月楼”跟阿兴师傅学做船点,后听说上海有个王致福师傅淮扬菜做得极好,就托朋友介绍去上海拜师取经。平日里则“在休息天也不闲着,在苏州的街头巷尾寻寻觅觅,与民间糕团师傅结为朋友,切磋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