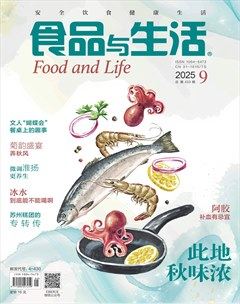换豆腐
我曾经下放的农场位于皖北,地处长江北岸。当时我们会在油菜和小麦收割以后的田地上种上黄豆。不同于连队种植的水稻、棉花,种植它所需的肥料及劳力不多,撒了豆种后至多锄上一遍草就等着收割了,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自然不会大面积种植,只是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之需,其他如绿豆、花生亦是如此。
农场生活艰苦,平日里没有什么好吃的,眼见得田里的豆子渐渐黄熟了,大家的“小心思” 也蠢蠢欲动了。女知青傍晚结伴去田里,但见昏黄暮色下绰绰黑影闪动,她们正猫着身子顺着枝茎采摘豆荚,这是属于知青版的“撸串”,待口袋都装得鼓鼓囊囊,才起身打道回府。
到宿舍后先将豆荚简单冲洗下。以前在上海家中做盐水毛豆是要剪去两头的,而此时却顾不上了,她们直接将一大堆豆子放在洗脸的铝盆里用清水煮,至多搁点盐粒。煮好后,一屋子的人围着铝盆吃得热闹,只是这一晚上屋内此起彼伏的肠鸣声,也是够热闹的,但为了口舌之欲,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男知青们不满足于此类“小打小闹”,他们要玩大手笔:这几日收工回家都要舍近求远,绕
去打谷场走一遭,将已经脱去壳、摊晒在场地上的黄豆捧起,朝自己口袋里装;为此好多人特意穿上了中山装,因为其口袋多且大,不消几日, 每人就有了好几千克的收获,至于是炒着吃还是带回上海孝敬父母,各人随意。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食品与生活》2025年9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